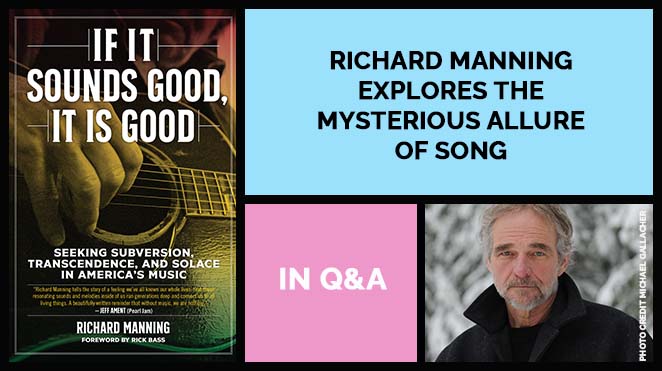玛丽·阿德金斯新小说的开端特权尽管我们对校园性侵的故事已经太熟悉了,但它仍然让读者感到痛心。一个naïve的年轻女子在住宿学院喝了太多的“潘趣酒”在兄弟会的房子,并在一个她几乎不认识的男人的卧室中失去了知觉。当攻击发生时,她太害怕和迷失方向而无法抵抗。第二天早上,以及接下来的一周里,她试图说服自己,她不是受害者,那个人也不是强奸犯。她的辩解很快就失效了。
 特权书中以令人钦佩的流畅笔触处理了袭击事件以及随后由校园纪律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用在了卷入此案的三位女性的内心冲突上。兄弟会派对上的年轻女子安妮·斯托达德(Annie Stoddard)来自乔治亚州的一个小镇,是一个害羞的二年级学生,她觉得自己被学术小团体和神秘的交配仪式所排斥。“我想和他们一样,”安妮说她的同学,“但不知道怎么做。”
特权书中以令人钦佩的流畅笔触处理了袭击事件以及随后由校园纪律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用在了卷入此案的三位女性的内心冲突上。兄弟会派对上的年轻女子安妮·斯托达德(Annie Stoddard)来自乔治亚州的一个小镇,是一个害羞的二年级学生,她觉得自己被学术小团体和神秘的交配仪式所排斥。“我想和他们一样,”安妮说她的同学,“但不知道怎么做。”
刚从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寄宿学校毕业的Bea Powers,已经报名参加了一个专门针对刑事司法改革的本科生选修课。Bea和Annie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州著名的卡特大学,对在校园咖啡店工作的Stayja York来说,这所大学就像一座真正的象牙塔,被学生忽视。对他们来说,Stayja是风景的一部分。
阿德金斯是纳什维尔的居民,她在她的主要人物之间轮换叙述视角,并立即确定他们的主要动机。八年级时,安妮的腿被严重烧伤,即使在夏天,她也用裤子掩盖她的伤疤。现在,她已经用教巴松管赚来的钱(她被卡特大学录取的秘密门票)支付了激光治疗的费用,她已经准备好穿裙子和短裤了——这是她性觉醒的代名词。Bea想要同时摆脱她母亲——一位成功的医生——的阴影,并重新平衡有利于富人和有关系的人的司法系统:也就是像她这样的人。Stayja是由一个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单身母亲抚养长大的,她“只有一个愿望胜过了所有其他愿望:摆脱贫困。”
阿德金斯通过与一个男人泰勒·布兰德(Tyler Brand)的邂逅将这些角色联系起来。泰勒·布兰德是一个富有家庭的后代,是一个有虐待倾向的连环魅力者。在安妮得知泰勒是多么邪恶后,Bea被指派为他的纪律听证会的“学生倡导者”。Bea开始对支持Tyler感到矛盾。“我是不是搞错了?”她问自己。“我是坏人吗?”与此同时,Stayja认为她在Tyler身上发现了一个在校园里和她一样看待Carter的人——也就是说,他是那些特权儿童的游乐场。在一个戏剧性的学期里,这三个女人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泰勒·布兰兹有了新的认识。
在阿德金斯的叙述中,特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泰勒·布兰德代表了光谱上的一个极端点。与他相比,Bea似乎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奋奋者,一个混血优秀生,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母亲在她高中毕业前就去世了。然而,在安妮看来,比娅是新英格兰一所著名寄宿学校的产物,她是一名精英,屈尊就读于南方的一所大学,却只为了加入一个排外的学术圈子。对于像安妮这样需要巴松管奖学金才能供得起卡特的农村公立学校女孩来说,比娅代表了有资格的阶层。
 安妮和比娅逐渐明白的是,所有一流大学的学生都享受着斯塔亚和她的同类们梦寐以求的优势。从斯泰亚的角度来看,卡特大学的学生并不是个体,而是一群毫无区别的人,他们“穿着印有小鳄鱼图案的鲜艳衬衫,或者穿着在斯泰亚看来像是孩子们生日装饰品的有图案的连衣裙”。它们甚至听起来都很像。“他们说话没有口音,好像他们来自任何地方,又不知来自哪里,”Stayja想。“他们的笑容太完美了。”
安妮和比娅逐渐明白的是,所有一流大学的学生都享受着斯塔亚和她的同类们梦寐以求的优势。从斯泰亚的角度来看,卡特大学的学生并不是个体,而是一群毫无区别的人,他们“穿着印有小鳄鱼图案的鲜艳衬衫,或者穿着在斯泰亚看来像是孩子们生日装饰品的有图案的连衣裙”。它们甚至听起来都很像。“他们说话没有口音,好像他们来自任何地方,又不知来自哪里,”Stayja想。“他们的笑容太完美了。”
阿德金斯对当代大学生活的描绘包括喜剧时刻,以平衡暴力和指责。她的大学生们在社交媒体上出丑,偶尔也会放下手机,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联系。Bea加入了一个即兴表演小组(名字用了一个不适合印刷的缩写词),据一个学生报纸的专栏作家说,“90%的学生都是清唱小组的成员。”
毕业于杜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阿德金斯让校园性侵问题变得清晰起来。对于那些质疑像安妮这样地位的女性是否会对泰勒这样的男人进行虚假指控的读者——作为对被拒绝的报复,希望获得一场利润丰厚的民事诉讼,或者出于其他自私的动机——阿德金斯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绝对不会。安妮不想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但她清楚地知道,“克服它”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相反,她知道她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找到我自己的平静”。

肖恩·金奇在奥斯汀长大,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他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现在在纳什维尔的蒙哥马利·贝尔学院教英语。
标记:伟德国际官网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