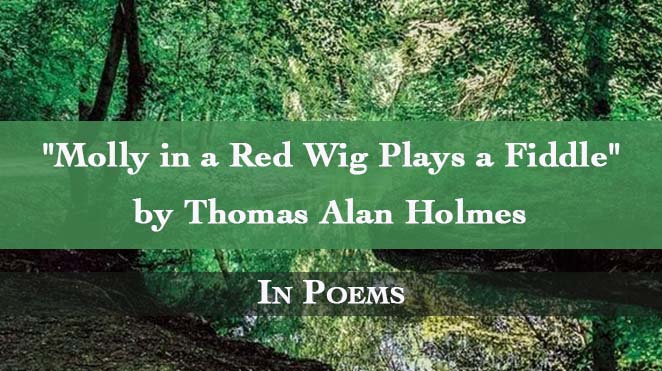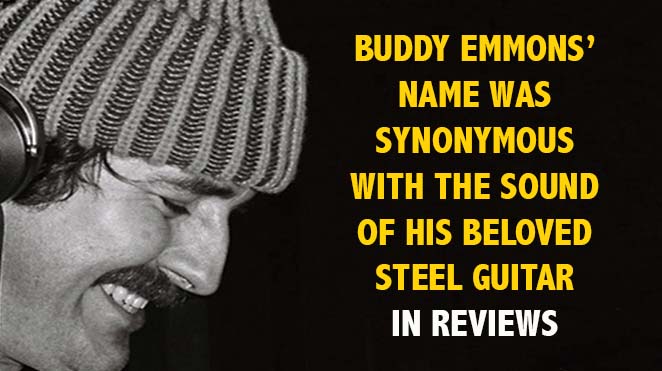田纳西州两位最资深的非虚构作家威尔·d·坎贝尔(Will D. Campbell)和约翰·埃格顿(John Egerton)相伴了半个世纪,坎贝尔于2013年6月3日因中风并发症去世。6月22日,在田纳西州朱丽叶山的圣斯蒂芬天主教社区举行的追悼会上,埃格顿这样纪念他的朋友和“珍本作家同行”:
如果我说得太久,有人会说阿门.
 1965年8月2日,我开始在纳什维尔的一家杂志工作。我刚满三十岁,和妻子和两个孩子从佛罗里达搬来。杂志坐落在皮博迪学院(Peabody College)校园附近一处杂乱的老房子里,我在二楼的办公室以前是一个带窗户的壁橱,只够放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还有一把椅子塞在一个角落里。
1965年8月2日,我开始在纳什维尔的一家杂志工作。我刚满三十岁,和妻子和两个孩子从佛罗里达搬来。杂志坐落在皮博迪学院(Peabody College)校园附近一处杂乱的老房子里,我在二楼的办公室以前是一个带窗户的壁橱,只够放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还有一把椅子塞在一个角落里。
那天早上,我见到了所有的同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得到了我的第一项任务。中午的时候,我正忙着研究这项任务。我听到门外楼梯上传来“砰”的一声,抬起头来,看到一个穿着牛仔服、戴着眼镜的男人,一绺波浪状的头发在一顶巨大的黑帽子宽阔的帽檐下晃来晃去。他站在那里疑惑地看着我,低声吹着口哨。我注意到他拄着一根雕刻过的拐杖,一条裤腿斜插在一双及小腿的牛仔皮靴上。我忍不住盯着那家伙看。他看上去大约有六十岁(事实上,他只有四十一岁),不知怎么的,他很淘气,嘴角上带着一丝讥笑。
“你是新来的吧?”他最后说,带着一种我觉得不赞成的神情打量着我。我结结巴巴地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他又直接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剪头发?”
“呃,没有,先生,我从来没有。”
“你不是说你不能吗?”
“呃,没有,先生,我只是从来没有....我想我可以,如果我必须这么做的话。”
他把多余的椅子从角落里拉出来,放在门口,朝外。他坐下来,脱下帽子,扭头说:“你桌子里有剪刀,是吗?所有记者都有一把剪刀。”我在抽屉里翻找,找到了所需的工具。“只要在脖子后面稍微修剪一下就行了。”他指示道。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甚至还没有交换姓名,也没有必要问一句“你从哪里来?”我成了威尔·戴维斯·坎贝尔的新理发师,我们开始了一段持续一生的友谊。
 现在他走了,今天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带来了自己与威尔亲密接触的故事,以及你们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生动记忆。我被赐予了恩典,这是我应得的特权,我可以歌颂他,代表我们在场的和不在的所有人,在他的骨灰上聚集和传播美好的话语。我怀着忐忑而热切的心情,怀着谦卑而充满信心地接受这个任务——希望我要说的话能引起你们所有像我一样了解他、爱他的人的共鸣。特别地,我祈祷我的话能安慰布伦达、佩妮、邦妮、韦布和孙辈们,并证明他们选择我与劳森牧师和其他人一起向我们亲爱的亲人、朋友和兄弟讲话、祈祷和唱告别歌是正确的。
现在他走了,今天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带来了自己与威尔亲密接触的故事,以及你们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生动记忆。我被赐予了恩典,这是我应得的特权,我可以歌颂他,代表我们在场的和不在的所有人,在他的骨灰上聚集和传播美好的话语。我怀着忐忑而热切的心情,怀着谦卑而充满信心地接受这个任务——希望我要说的话能引起你们所有像我一样了解他、爱他的人的共鸣。特别地,我祈祷我的话能安慰布伦达、佩妮、邦妮、韦布和孙辈们,并证明他们选择我与劳森牧师和其他人一起向我们亲爱的亲人、朋友和兄弟讲话、祈祷和唱告别歌是正确的。
在第一次见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威尔·坎贝尔到底是谁感到困惑——这个有趣、无礼、贤明、犀利的密西西比州乡村男孩,从捡棉花的人变成了耶鲁大学神学学者,后来又变成了终身的南方人。在我遇到他之前,他曾在浸礼会的讲坛上做过牧师,在大学里做过牧师,后来又在南方种族冲突频发的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担任外交使团。从1965年开始,他的最后一份正式工作是在一间小木屋里,与一群南方宗教激进分子一起,他们对圣经中的好消息——“你已经被原谅了”——的解释,使左右两派的宗教机构非常恼火。
这群形同无形的激进分子自称为“南方教会人士委员会”,他们靠私人礼物和基金会的资助维持生活——这些钱只够威尔为那些因数百年来种族非人化的遗留问题而深受创伤和毁容的南方黑人和白人进行个性化和个人主义的传道工作。
 我只是匆匆瞥见了“早期”的威尔。据说,他开着一辆奔驰,喝着霞多丽酒,穿着粗花呢衣服,戴着苏格兰帽,穿着牛津鞋,抽着烟斗。我现在意识到,“新的”威尔正在换装,这可能会让一个公开宣称的融合主义者更容易在紧张的南方“通过”。坎贝尔一家离开了郊区的三居室牧场房子,搬到了威尔逊县的一个农场,威尔的装备很快就成了他的标志:古怪的帽子、帽子和手杖、靴子和蓝色牛仔裤、嚼烟草、威士忌、拖拉机、一匹马、一只狗和一只山羊、一辆旧皮卡车,后窗户上有一个枪架。
我只是匆匆瞥见了“早期”的威尔。据说,他开着一辆奔驰,喝着霞多丽酒,穿着粗花呢衣服,戴着苏格兰帽,穿着牛津鞋,抽着烟斗。我现在意识到,“新的”威尔正在换装,这可能会让一个公开宣称的融合主义者更容易在紧张的南方“通过”。坎贝尔一家离开了郊区的三居室牧场房子,搬到了威尔逊县的一个农场,威尔的装备很快就成了他的标志:古怪的帽子、帽子和手杖、靴子和蓝色牛仔裤、嚼烟草、威士忌、拖拉机、一匹马、一只狗和一只山羊、一辆旧皮卡车,后窗户上有一个枪架。
但变化不止于这些外在的表象。在他的脑子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当民权运动回到纳什维尔时(1957年学校废除种族隔离,1960年食堂静坐抗议,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威尔看到社会的支柱机构——教堂、学校、公司、政府——并没有解决种族隔离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办法;事实上,他们是问题的核心。
20世纪60年代初的四个夏天,威尔在研讨会上为来自南方白人和黑人大学的精选学生群体演讲。他视他们为明日的领袖,即将与一个不道德的权力结构发生冲突,他试图向他们传达一种信念、忠诚和忍耐的信息。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他反问,“我们希望完成什么?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种族危机,我多次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感受到南方的悲剧,我继续前行,因为在上帝的庇下,我别无选择,只能表现得好像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我的肩上——同时我也知道我个人什么都没有完成。”
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史前部落互相攻击的寓言,“不是因为他们危险或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威尔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战士身上。一天清晨,他从战场上回来,看到一根羽毛在海滩上飘扬,就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它没有价值,没有实际用途,但它很漂亮,色彩斑斓,柔软——不知怎的,它道出了他最深的感情。他把它带回了他的洞穴,当他把它拿给别人看时,它的美丽似乎绽放了。“有了那根羽毛,”威尔告诉学生们,“文明和人类关系开始了。”
但是,他接着说,从那以后,我们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仍然在另一个部落的夜晚肆虐——越过浩瀚的海洋和狭窄的午餐柜台,用氢弹和铅管,立法和宣传,关闭的校舍和燃烧的公共汽车....人际关系开始于一个观点,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一种偏见,但它可以发展成……更深层次的东西。它确实与美学有关,与真实、公正、纯洁、可爱、高尚有关。这是关于我们与万能的上帝之间的事情。”

1964年,威尔在夏季研讨会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他仍在尽最大努力成为一个忠实的机构基督徒,但他和机构都在放松控制。最后,在1965年8月——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月晚些时候——他开车去了阿拉巴马州的费尔霍普,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顿悟,这标志着他的皈依。
威尔的弟弟乔正在与毒瘾作斗争,他去费尔霍普拜访了P.D. East,他是一位打破传统的前密西西比人,也是坎贝尔兄弟的朋友。伊斯特机智伶牙俐齿,说话方式令人羡慕。正当白人至上主义的白玉兰面纱开始打开时,他在哈蒂斯堡附近的佩塔尔村买了一份小报纸。发现自己不断陷入困境,他最终被迫与他的家人逃离,但他带走了花瓣纸并不定期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出版,面向为数不多但忠实的地下订阅者。乔跟踪他到了费尔霍普,然后自己也去了那里,带着他的恶魔。很快,警察叫威尔过来帮忙。
他在下午晚些时候到达,没有任何突发新闻,发现他的朋友和兄弟在树荫下悠闲地喝啤酒。
“你认识一个叫乔纳森·丹尼尔的人吗?”P. D.随口问道。威尔确实认识他——一个来自新英格兰的温柔的年轻神学院学生,他来到阿拉巴马州,帮助寻找一条和平的种族正义之路。
“一个叫汤姆·科尔曼的人今天下午用猎枪把他打死了,”伊斯特报道。“把他杀了。”
威尔崩溃了。他强忍着眼泪,与那些不知道教会的人通电话,还有记者、律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司法部。直到深夜,这三个人还在厨房的桌子上徘徊,吃吃喝喝,争吵不休。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宗教。
他永远不会忘记接下来发生的事。“你认为你的朋友耶稣先生对这些杀戮有什么看法?”警察问他。威尔还没来得及回答,警局就让他给基督教信仰下个定义。“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信息是什么?告诉我吧。”
威尔感到受了伤,心里很有防备,他呆呆地坐着,一言不发。然后他说:“我们都是混蛋,但上帝仍然爱我们。”
“乔纳森是个私生子吗?”P.D.紧随其后。威尔支支吾吾,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但最终承认,是的,即使是幸福的乔纳森也是个私生子。
“还有汤姆·科尔曼吗?”
“这很简单。是的,当然。”威尔回答。
警方包围了他们。"你觉得你的耶稣先生和他爸爸最爱哪个混蛋"
在他最伟大的著作中,蜻蜓的兄弟威尔把这个故事推向了紧张而痛苦的高潮。“突然之间,”他写道,“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一切。这是一个启示。”他开始呜咽,抽泣,然后笑了起来:“我是嘲笑自己,在20年的一个部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寻找政府的自由部成熟…来验证和验证我们的道德,敬拜靖国神社的学术界,使最高法院的偶像和神学的法律和秩序,不仅拒绝相信我的,但我自己的历史和我的人民——托马斯“祝:爱(上帝)。如果爱过,就原谅。如果被原谅,就会和好。”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在南方教士委员会的新季刊上,Katallagete(希腊语“和解”的意思),威尔写道:“当托马斯杀死乔纳森时,他对阿拉巴马州犯下了罪行。阿拉巴马州出于自己的原因,选择不惩罚他的罪行。当多马杀死约拿单时,他也犯了对神的罪。奇怪的,近乎疯狂的是,这两个被冒犯的当事人做出了相同的判决:……无罪释放。”
这是新的威尔·坎贝尔,通往费尔霍普之路的皈依者:旧的威尔穿着不同的制服,对南方/美国/人类的困境有更深刻和更复杂的理解,对一个我们无力修复的破碎世界的不可言喻的悲剧有更深刻和更复杂的理解。这就是我在48年前那个八月的日子里第一次见到的威尔。
 他与众不同,但为人所熟悉:一个充满矛盾的南方人。他是一个信徒,也是一个怀疑论者。他透过玻璃,黑暗地看着,为受害者和不人道的肇事者哭泣。他在马太福音中听到耶稣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你有什么成就呢?就连银行家和酒保也这么干。不,那还不够。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得爱他们所有人。
他与众不同,但为人所熟悉:一个充满矛盾的南方人。他是一个信徒,也是一个怀疑论者。他透过玻璃,黑暗地看着,为受害者和不人道的肇事者哭泣。他在马太福音中听到耶稣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你有什么成就呢?就连银行家和酒保也这么干。不,那还不够。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得爱他们所有人。
新的威尔和旧的威尔一样,心里明白,无论他做了什么,做得有多好,都是不够的。他不是圣人。说他爱每一个人也不完全是真的。他有时会表现出一种复仇的冲动——一种温顺的、迂回的、消极的攻击行为。他夸口说他从未投票给“凯撒先生的跟班”,但他撒谎了——我看到他在投票站排队等候投票。他的家庭是最重要的,但并不总是最重要的。他和我们很像——也许做得更好,但他仍然是威尔。
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他有一种神秘的技巧,能深入人们的内心,让他们觉得自己对他很重要,很重要。穷人、无家可归的人、被监禁的人、贱民都觉得他关心他们。他赢得了南方和全国非裔美国领导人的信任和尊重,当时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需要信任。他是工人阶级的盟友——农民、劳动者和服务业,我们现在都依靠在他们的肩上。在教堂尖塔内外,许多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都从威尔兄弟那里得到了启发。乐坛的人拥抱他,他也以十倍的爱回报他们。学者、律师、医生都是如此。做文字和图片的人,也就是我们做墨水和纸张交易的人,认为他也是一个瘾君子。他属于我们大家,我们也属于他。
所以我们这次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后的话是他说的。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在一本未完成的书的序言中这样描述自己:
我是一名传教士。各种各样的。但在任何传统的部长级努力中,我从来没有做大,也从来没有出名,我也从来没有在一份真正的工作上干很久。至少在机构的世界里不是这样。我每年都主持了大约二十场婚礼,也主持了差不多同样多的葬礼。我参观了医院、监狱和疗养院,很多人定期过来谈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你可以说,他们成了我的信徒。专业人士称之为咨询。我称之为拜访朋友和邻居。我仍然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If you want to think of it as a scattered parish, a church without a steeple—and me as its pastor … tending the flock—that’s all right with me.
“好吧,就这样吧,”他会这样对我们说,就在这时。“把它放在院子里。是的,祈祷。待会儿见。”
有人说阿门.
版权所有(c) 2013 by John Egerton。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