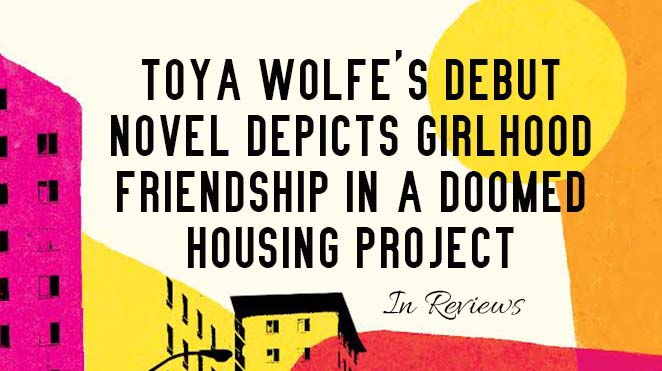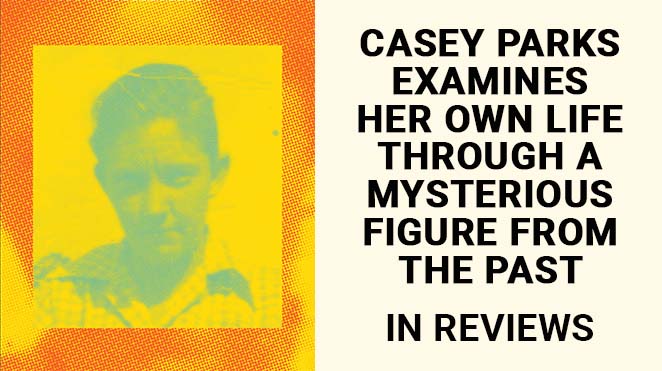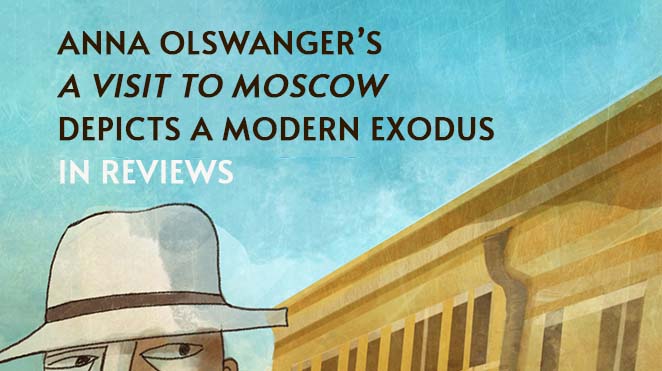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13个月后,我得知祖母患上了晚期胰腺癌,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我决定从和平队辞职,放弃了在一个穆斯林村庄当英语老师的生活,换取了最后一次见到祖母的机会。四十八小时后,我将从拥挤闷热的家中突然告别,过渡到在纳什维尔有空调的宁静中提前打招呼。
 新闻从我在当地的红颜知己Kiky开始传递,她几乎是我年轻印尼女性形象的延伸,然后转移到我的邻居、寄宿家庭和学校。没有完全的理解,没有足够的安慰。Kiky打破了我们传统的问候方式——握手和脸颊按压——来了一个大大的、非印尼式的、充满泪水的拥抱。我一直告诉她,也一直告诉自己,在爪哇有一个悲伤的朋友,在纳什维尔就有一个快乐的朋友,为我回家而高兴。“我觉得我的大脑要爆发了,”我告诉Kiky,旁边的一个学生看起来很不安。“我很困惑,”我说,“但这是对的,我知道。”
新闻从我在当地的红颜知己Kiky开始传递,她几乎是我年轻印尼女性形象的延伸,然后转移到我的邻居、寄宿家庭和学校。没有完全的理解,没有足够的安慰。Kiky打破了我们传统的问候方式——握手和脸颊按压——来了一个大大的、非印尼式的、充满泪水的拥抱。我一直告诉她,也一直告诉自己,在爪哇有一个悲伤的朋友,在纳什维尔就有一个快乐的朋友,为我回家而高兴。“我觉得我的大脑要爆发了,”我告诉Kiky,旁边的一个学生看起来很不安。“我很困惑,”我说,“但这是对的,我知道。”
我周三离开;我需要准备我的包。在机器人模式下,我把东西从梳妆台里拿出来,扔进去首页而且捐赠成堆,大声说:“带回家。捐款。捐款。捐款。我在做什么?捐款。继续。带回家……”我想到了一大堆我看不出有什么运输意义的东西。消息一传开,管家和我的接待姐姐就像穆斯林在他们从未见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早晨一样开始了争吵。 “Really?” they say, “You no bring this?”
因为我的护照要三个小时才能到移民局,所以我没有时间在离开之前回到学校。它们在周二晚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我寄宿家庭的客厅。教师、学生、管理员。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滔滔不绝的爱。我看到那些我从未想过会如此伤心的人流下了眼泪;我收到的祝福、关心的声明和印尼人对我想象中的错误的道歉比我应该得到的还要多。回家看祖母——这句话很容易翻译。没有印度尼西亚人会质疑在亲人即将去世时陪伴的必要性。但随后我又会想,为什么我以后不能再回头看它们,于是我尽我所能解释一个无法解释的观点。
 “这很难解释,”我用印尼语说。“这里就像一个世界。那里像世界其他。在这两个地方我都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但如果我回到另一个世界,以后对我来说太难再回来了。”
“这很难解释,”我用印尼语说。“这里就像一个世界。那里像世界其他。在这两个地方我都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但如果我回到另一个世界,以后对我来说太难再回来了。”
他们大概会明白:“啊,耶。我们觉得很沉重,失去了苏菲。像损失大。”
“是的,我也是。像损失大。很难过,分裂。这里的每个人都伤心;每个人都有快乐。这里有家的感觉,那里也有。”
“啊,是啊,是啊……”他们点了点头,他们得到的答案也许和我所希望的一样多。
和平队是什么,就是这个带着木偶线带领我度过乡村生活,完成课程计划,吃碗饭,泡桶浴的东西?这不是一场马拉松,也不是一集需要你奋战到底的《幸存者》。这是一个人可以进入的工作,也是一个人可以退出的工作。你在旅途中,坐在一辆公车上,感觉它会白白停下来。但如果在某个地方,一个标志指向另一个方向的乘客,那么,无论如何,门都可以打开,司机会好心地提醒你,和平队只是另一艘船,你可以随意上下。一年可能足够了;外面的事情可能更重要。我从未想过要离开,但突然间,我无法留下。
知道一个人能在这么小的地方对这么多人意义重大,真是太好了。后来,望向窗外,我想起了泗水灯火阑珊处的所有小村庄,每一所小学校都只是岛屿上的一个小点,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小点。这么多的点,这么多的爱。在这个点上放一个志愿者,看着爱滚滚而来。
我永远不会失去与阿森巴古斯的联系,但我觉得我在一个地方死去,在另一个地方走向重生。我在慢慢地成形,成形再成形,也许只是为了再成形再成形。
我敢肯定,回家也会带来奇怪的事情。这是一种不同的孤立,只有我知道印尼是什么,我在那里的时候是什么,家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
 新加坡航站楼的移动人行道给人一种科技感、金属感和不舒服的快速感,以至于我不得不走到安全的地毯上,用腿以人类的速度走完剩下的长度。机场是一个闪闪发光、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怪物。总有一天我会很高兴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所有这些东西,但现在我只能坐下来。我在肥皂分配器上遇到了麻烦,在开灯上也遇到了麻烦。我发现自己在说:“世界是什么?他马上就要开始写一本哲学书了。
新加坡航站楼的移动人行道给人一种科技感、金属感和不舒服的快速感,以至于我不得不走到安全的地毯上,用腿以人类的速度走完剩下的长度。机场是一个闪闪发光、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怪物。总有一天我会很高兴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所有这些东西,但现在我只能坐下来。我在肥皂分配器上遇到了麻烦,在开灯上也遇到了麻烦。我发现自己在说:“世界是什么?他马上就要开始写一本哲学书了。
在这个门口等待的人看起来很老练。他们很安静,不会盯着看,也不会说奇怪的话。没有人吸烟,蹲着,吐痰。没人拔胡子或剔牙。
和匿名!我环顾四周,心里想,嘿,你不想看看我吗?我很特别,很有趣。但我大部分人认为,谢谢,谢谢你知道我是人类。谢谢你没有用手机拍我的脸。
当我们出发去东京时,我前面的男孩转过身来和我闲聊:“你要去哪里?”他有南方小镇的口音,我很熟悉。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卡伯勒往南一小时车程。他不问我从哪里来,赞美真主。我无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的眼睛困在一种如此疲惫,如此睁大,如此过度刺激的状态。
我试着看飞行中的《顶级大厨》,但实际上我的大脑在打转。他们在谈论煎蛋卷。你那南方口音离我一个座位远。没有煎炸油的迹象。而且,尽管我现在不再在赤道上大汗淋漓,需要用乳液洗澡,但我暂时感到满足。
南方男孩终于问我从哪里来。“那又怎样,你在新加坡出差吗?”
“不,我当时在印度尼西亚。”
“什么?只是参观?”
“不,我在那儿一年了。”
“哦,做什么?”
“我在和平队(Peace Corps)教英语;现在我要回家了。”
然后,“那你回家后要做什么?”
亲爱的上帝。我欣赏你的口音。很高兴,真的。但你不能再问我问题了。请停止。现在请停止。
 我很想在东京机场买点零食,但我只是绕着圈子走。卢比是无用的。零食看起来很奇怪。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避难所——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理解我的性格,欣赏我的人性,这足以令人欣慰:Kiky,我的邻居,学校食堂的老师们。我可以坐着,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没有被观察。现在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天堂,至少我正在踏入的这个世界是这样。我不是局外人;我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人们满口脏话,比如旧金山,佛罗里达鳄鱼队,希尔顿黑德。婴儿少了这么多! (Much less? Fewer? Many fewer? Much fewer?) And the water in the water fountain is so, so cold.
我很想在东京机场买点零食,但我只是绕着圈子走。卢比是无用的。零食看起来很奇怪。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避难所——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理解我的性格,欣赏我的人性,这足以令人欣慰:Kiky,我的邻居,学校食堂的老师们。我可以坐着,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没有被观察。现在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天堂,至少我正在踏入的这个世界是这样。我不是局外人;我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人们满口脏话,比如旧金山,佛罗里达鳄鱼队,希尔顿黑德。婴儿少了这么多! (Much less? Fewer? Many fewer? Much fewer?) And the water in the water fountain is so, so cold.
现在我点了一杯红酒,天哪,德尔塔的菜多得很。这是荒谬的,真的是疯狂的,我可以在飞机上免费得到这么多的红酒,但必须坐6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从现场到泗水,为了一瓶昂贵的葡萄酒,即使在首都,似乎它真的不属于爪哇的边界。
现在我想象飞机坠落的情景。我没办法。我们是碰撞。但我在想如果我在过去的五天里有什么感觉那就是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小轮子把东西送到它们需要的地方。现在我要去见我奶奶。我不会不见我奶奶的。我等待一切顺利。我知道它会来的。
在爪哇,他们喜欢你和他们在一起时的样子。他们养育它,塑造它,形成与它的家庭关系。但是他们不能知道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你不是你的那部分,你被抑制的那部分,甚至完全改变了,这要感谢文化规范、行为模式、沟通失误,以及归根结底有着深刻而不同根源的理解。
 我可以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家庭。毫无疑问,我可以选择巴帕克,伊布,姐妹,最好的朋友。我可以爱他们,欣赏他们,为他们履行某些职责。但这永远改变不了我有一个家庭的事实——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而我所在的印尼村子里的那些人,忙于对我的看法产生依恋,无法理解我的观点。他们从来没有被单独扔进一个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社会。
我可以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家庭。毫无疑问,我可以选择巴帕克,伊布,姐妹,最好的朋友。我可以爱他们,欣赏他们,为他们履行某些职责。但这永远改变不了我有一个家庭的事实——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而我所在的印尼村子里的那些人,忙于对我的看法产生依恋,无法理解我的观点。他们从来没有被单独扔进一个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社会。
移动地图上的飞机触及阿拉斯加的西端。西班牙的图像是Mar de Bering和Estados Unidos。语言。这么多!这张英文图片显示了阿拉斯加城市上的黄点。鱼村。山村。也许美国和爪哇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
底特律机场是一座安静的冰屋。人们给我打电话亲爱的,亲爱的,蜂蜜.“你去印尼的目的是什么?”移民先生说。
“我是和平队的。”
“欢迎回家,亲爱的。”如果我现在和我的大脑有任何联系,我会微笑回应。
纳什维尔如此简单,如此干净,就像一本故事书。我们还不如降落在一床西兰花上;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树梢。达美航空的员工在追踪到我丢失的行李后,告诉我祝我过得愉快。追踪那件行李比在印尼银行做任何事都要容易一亿倍。
我的父亲接我,我们走到房子,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人在路边。没有当地人坐着,看着,挂着,吃着。它只是平静,无声。没有干扰,没有混乱,没有拥挤的人群。
一切都是冷的。我的菜。我的早餐勺子很重。牛奶很好,但凉得不舒服。空气是安静的寒冷;如果我没有被冻死,我就会利用现在自由的机会穿一件背心。
妈妈的电话。她和我祖母在阿拉巴马州。“今天早上奶奶问她的娃娃在哪里,”她说,并解释说奶奶变得更像孩子了。“你的洋娃娃吗?”妈妈问她。
“你知道,”奶奶说。“索菲娅!”
我确信我做的是对的。我留在爪哇的人说:“是的,如果真主阿拉想要的话。”也许不是真主阿拉,而是某个地方的什么东西,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版权(c) 2013由Sophie Sanders。保留所有权利。苏菲·桑德斯是纳什维尔Harpeth Hall学校的毕业生。她拥有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心理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她现在住在纳什维尔,正在追求各种形式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