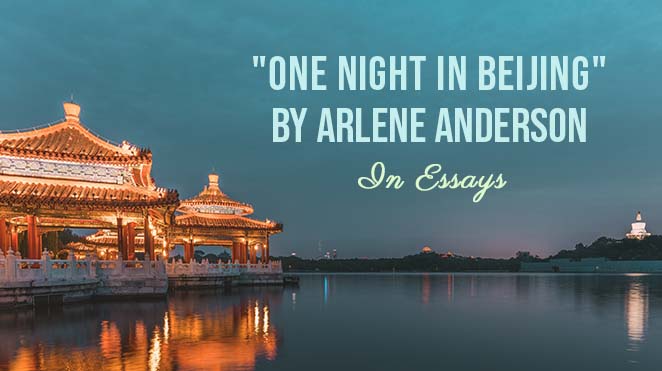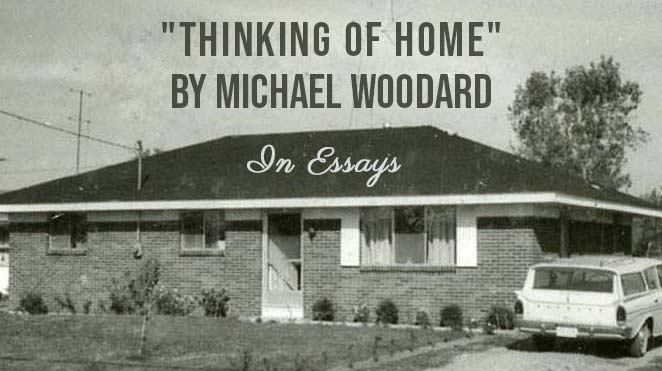它是那种在庭院拍卖中可能卖不到一毛钱的东西。这个铝制量杯由于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磨损了,除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当它的手柄掉下来时,我的反应完全不可理喻。我像捧Fabergé鸡蛋一样捧着那个被肢解的手柄,问丈夫能不能把它粘回去。作为交换,我得到了一个“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的白眼。我以为你没有。
 近年来,这个量杯——大约在1960年,满容量装着两个杯子——一直呆在我们的特百惠干狗粮箱里。里斯急切地期待着铝耙过他的狗粮的声音。一天两次,杯子完成了它的工作,在剩下的一天里休息,因为它是一个老人。
近年来,这个量杯——大约在1960年,满容量装着两个杯子——一直呆在我们的特百惠干狗粮箱里。里斯急切地期待着铝耙过他的狗粮的声音。一天两次,杯子完成了它的工作,在剩下的一天里休息,因为它是一个老人。
我们对那些我们甚至不认为是财产的小东西产生了依恋,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些东西如果被困在荒岛上,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必需品。然而,它们却以某种方式触动了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我们微笑。
这个特殊的量杯是我母亲厨房里的主要物品——用来装自制的燕麦饼干、生日蛋糕和奶油糖果布朗尼。我记得我从滤菜器里偷了它,用在我的粉色塑料玩具厨房里。在我做第一个非易烤烤箱的那天,我也用了它,真正的香蕉面包。当妈妈为我从大烤箱里拿出面包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期待。我踮起脚尖往锅里看,只发现了一层薄薄的烧焦的粘稠物。我小心翼翼地用我的量杯朋友来测量所需要的糖,但在兴奋中忽略了所需要的面粉。平底锅已经无法挽救了,但妈妈和我一起拿我的钱开怀大笑。
厨房里铺着黑白相间的瓷砖,母亲的围裙边上有红色的褶边。当然,我并不是每次去喂狗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些事情,但在我脑海中的某个地方,在我心中,那些画面一直挥之不去。他们是我一天中不请自来的祝福。
在丈夫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我决定继续使用没有把手的量杯。毕竟,它还是抢先了。然而,有两次,锯齿状的金属边缘夹住了我的手指。我不知道我还能流多少血。我拿了一把结实的指甲锉,在粗糙的指甲上刮了一下,一直在想,是不是该把量杯收起来了。
 我们家还有更值钱的东西,我永远不能放弃。这是我姨婆丽莎(Liza)的镂空玻璃酒杯,放在我们餐桌中央。当我还小的时候——大概和我烤香蕉差不多大的时候——我的姨婆杰西经常带我去她姐姐莉莎家玩一天。(我们家肯定有上了年纪的亲戚,其中大多数未婚或丧偶。)也许这听起来像一个孩子打发时间的可怕方式,但我期待着那些日子。虽然莉莎阿姨坐在轮椅上,话不多,但她耐心地听我给她讲我所有娃娃的名字和生活故事。杰西给我们做了小黄瓜三明治和甜椒奶酪饼干,配上橄榄和面包和黄油块作为装饰,我们会在电视托盘上的柳条瓷器上吃饭,一边看我看不懂的肥皂剧。甜茶盛在精致的水晶玻璃杯里,我觉得自己很成熟。
我们家还有更值钱的东西,我永远不能放弃。这是我姨婆丽莎(Liza)的镂空玻璃酒杯,放在我们餐桌中央。当我还小的时候——大概和我烤香蕉差不多大的时候——我的姨婆杰西经常带我去她姐姐莉莎家玩一天。(我们家肯定有上了年纪的亲戚,其中大多数未婚或丧偶。)也许这听起来像一个孩子打发时间的可怕方式,但我期待着那些日子。虽然莉莎阿姨坐在轮椅上,话不多,但她耐心地听我给她讲我所有娃娃的名字和生活故事。杰西给我们做了小黄瓜三明治和甜椒奶酪饼干,配上橄榄和面包和黄油块作为装饰,我们会在电视托盘上的柳条瓷器上吃饭,一边看我看不懂的肥皂剧。甜茶盛在精致的水晶玻璃杯里,我觉得自己很成熟。
我清楚地记得莉莎阿姨自助餐上的潘趣酒碗。当杰西离开房间时,我用绣花挂毯凳够到碗。我在那里跳上跳下,给我的娃娃们奉上想象中的潘趣酒。
“我也想来点潘趣酒,”莉莎阿姨说。杰西重新走进房间,告诫我不要玩弄这样一位宝贵的美人。
“这不是玩具,”她责备道。
“嘘,”莉莎姨妈告诫说。“让她玩吧。”
莉莎阿姨去世时,让我非常高兴的是,她在遗嘱中留下了一条遗言,说我将继承她的潘趣酒碗和杯子。直到今天,我还会把它扔进着火的房子里。除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没什么价值。因为,你看,只有我知道里面的甜酒有多甜——就像只有在我的脑海里,我才能看到妈妈纤细的手指爬上那只旧量杯的顶部,为我的生日蛋糕平整面粉。
我们紧紧抓住童年的零碎片段,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清晰地表达,甚至没有完全意识到,它们提醒着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谁。他们讲述我们的故事。我再也不能坐在我妈妈黑白相间的厨房里高高的金属凳子上,看着她做饭和烤面包,我再也不能听我的姨婆们嘀咕肥皂剧女主角。我不得不穿上职业装、查看日历、加油、买洗发水、忍受乳房x光检查、支付账单、清理邮件。虽然我完全处在成年人的责任范围内,但偶尔手指上的划痕也值得我为它所激发的青春瞬间闪现。
坚持意味着不放手吗?也许这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也许把这些琐碎的、转瞬即逝的日常提醒——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口袋里,能让我们继续前进。生长。
我曾经是个孩子,但现在不是了,养我的人也都去世了。这就是生命的循环,我很平静。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内心深处抓住那个小女孩。
她做的潘趣酒最好。

版权所有©2021 by Melissa Norton Carro。版权所有。作为土生土长的田纳西人,梅丽莎·诺顿·卡罗拥有超过20年的沟通经验。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学士学位,目前在该校工作。卡罗是一名多年的秘密小说作家,同时抚养着三个女儿,他写了一篇博客,在中间,讲述三明治世代的生活。摩利亚山守灵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她正在写另一部。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