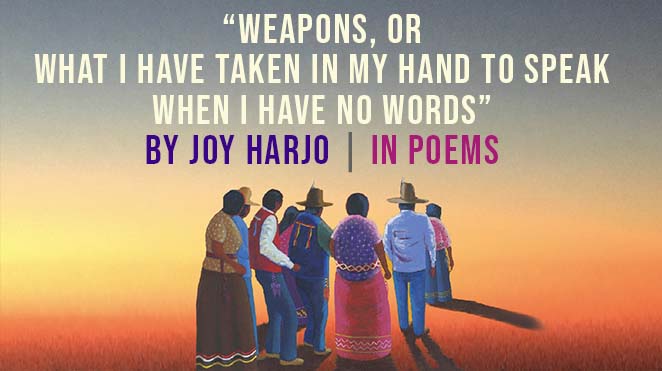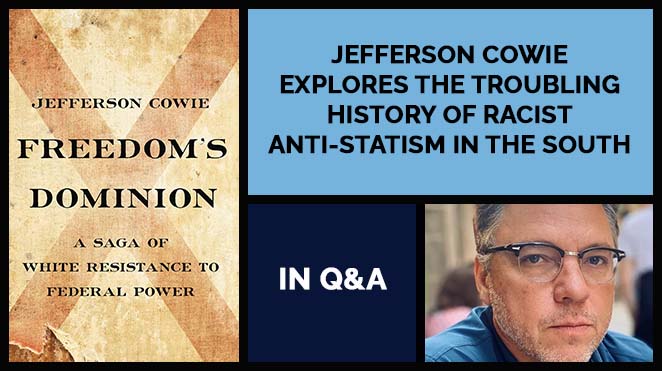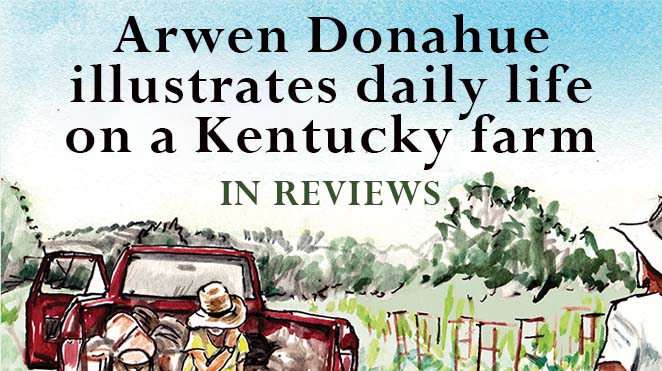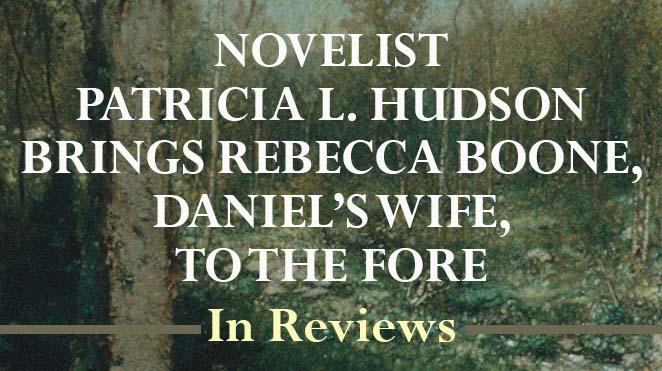我在白人中的时光小说作家Jennine Capó Crucet的散文集回忆录,开篇讲述了她作为古巴裔美国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进入康奈尔大学的经历。这个故事和书中许多故事一样,既有趣又令人震惊。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她写道,“但我们在学校发来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答案:我的家人应该在一年级新生迎新会上待多久?”在没有得到答案的情况下,她的父母、祖母和妹妹攒了几个月的钱,在伊萨卡预订了一个星期的住宿,他们以为这是为全家人准备的迎新活动,结果在院长的欢迎辞后被打发走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留下了,买课本,跟着克鲁塞特注册上课,一起在餐厅吃饭,她的母亲像在家一样用餐巾和叉子摆放餐桌。
克鲁塞特以一个在迈阿密出生和长大的古巴裔美国人的独特视角,以温柔、幽默和毫不犹豫的坦率,探索了第一代美国人的广泛经历。她解释说,由于古巴人和古巴文化在这座城市占主导地位,“在迈阿密,古巴人就是一种白人,拥有白人所能提供的所有特权和文化中立感。”
然而,作为难民,她的父母对自己的处境有不同的理解。克鲁塞特回忆说,作为一个女孩,她“很大声,经常开玩笑,我最好的材料直接抄袭布偶,主要是福齐熊。”她的母亲会把她和她的一个同学,一个安静的、传统意义上很漂亮的白人女孩进行比较,有一次甚至说她希望阿曼达是她的女儿。克鲁塞特在她的回顾评估中坦率地说:“她理想中的女儿是一个白人女孩,因为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作为拉丁裔,我们会受到低人一等的对待,我们是某种程度上较小。她只是想让我过得更好,这意味着:更白。”
 离开迈阿密后,克鲁塞特的每一次经历都帮助她摆脱了内化的白人身份。刚进大学时,她并不知道自己会是康奈尔大学为数不多的拉丁裔或西班牙裔学生之一,甚至不知道别人会以那种普遍的方式看待她。在迈阿密,她是古巴人,“认为每个地方都像我长大的地方一样,原籍国的区别非常明显,因此永远不会被抹去。”在大学里,我成为拉丁裔是为了寻找社区,为了生存。”
离开迈阿密后,克鲁塞特的每一次经历都帮助她摆脱了内化的白人身份。刚进大学时,她并不知道自己会是康奈尔大学为数不多的拉丁裔或西班牙裔学生之一,甚至不知道别人会以那种普遍的方式看待她。在迈阿密,她是古巴人,“认为每个地方都像我长大的地方一样,原籍国的区别非常明显,因此永远不会被抹去。”在大学里,我成为拉丁裔是为了寻找社区,为了生存。”
在幽默的文章《说我愿意》中,23岁的克鲁塞特正在计划她和大学男友的婚礼,他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白人。最棘手的问题是为招待会选择音乐。克鲁塞特的母亲坚持雇用古巴DJ弗雷迪·J (Freddy J),他的解决方案是“把所有美国人赶出去”,以弥合她的古巴家庭和未婚夫的中西部部落之间的文化分歧。他们不跳舞。他们不没有什么.它们是干的,它们会一直放在那里,所以这是第一步,忘了它们。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多年后,她离婚了,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在同一栋大楼里租了一间阁楼,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婚礼场地,在一个又一个周末里,她了解了白人婚礼文化和在其周围旋转的dj,比她想知道的要多。
在她最尖刻的一篇文章《想象我在这里:或者,我是如何成为一名教授的》中,克鲁塞特回忆了她最近作为客座讲师遇到的一名学生。这名年轻的白人女性在讨论高等教育机构中公平的教师代表权时变得焦躁和愤怒,她声称故意雇用有色人种的教师来纠正历史上的不平衡是“种族主义”。这个学生继续争论,直到把自己都弄哭了。谈话结束后,克鲁塞特写道:“我忍住了想走到她身边,蹲下来,进一步吸引她的冲动。我忽略了这个白人妇女的泪水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忽略它们更岌岌可危之时,转向群四个女人的颜色和两个白人女性物化在舞台前,学生同样重要,他们每个人抓住我的小说——约一个女孩很像他们,做他们在做什么,在胸,就好像它是一种新的护甲。”
克鲁塞特的观点无畏而有趣,虽然她不避讳揭露不平等、偏执和各个方面的功能障碍,但她也以温柔和尊重的态度对待那些在她个人历史中出现过的人、地方和情况。我在白人中的时光对美国白人的异类经历进行了敏锐而感人的描述。

Kathryn Justice Leache住在她的家乡孟菲斯。她为BookPage并担任孟菲斯独立书店Novel的社交媒体和促销协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