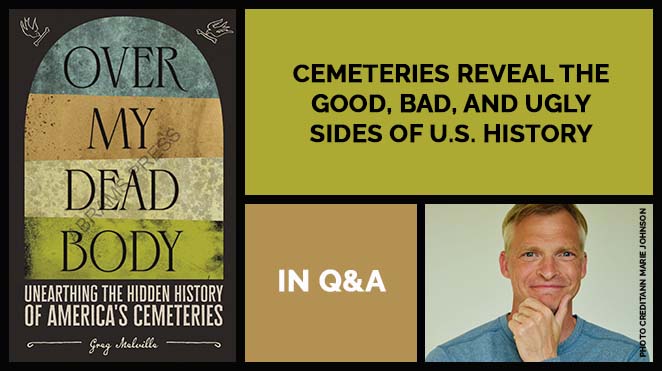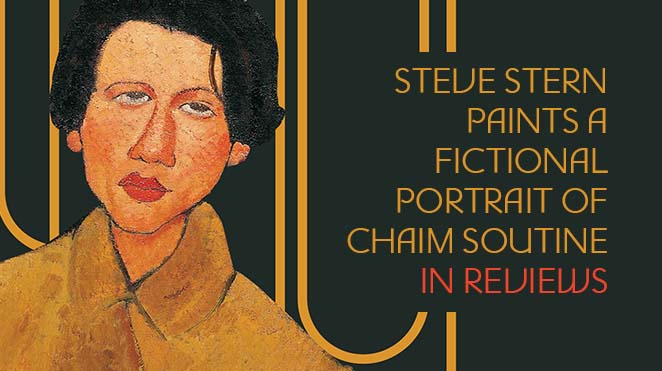迈克尔·格里菲斯谦恭地说,他的书还没有使他有资格成为“世界历史人物”会说话的石头:墓地讲述的故事他完成了一项他所描绘的政治家、实业家和艺术家都无法完成的壮举:他让死者起死回生。
 这本书的构思似乎并不宏大——它记录了埋葬在辛辛那提斯普林格罗夫公墓和植物园的人们的生活——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些文章追踪历史与个人之间微妙的交叉,它们提醒我们,骄傲和野心会无情地导致遗忘。格里菲斯同时加深了我们对孤独生活的同情,并惩罚了我们对永生的幻想。
这本书的构思似乎并不宏大——它记录了埋葬在辛辛那提斯普林格罗夫公墓和植物园的人们的生活——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些文章追踪历史与个人之间微妙的交叉,它们提醒我们,骄傲和野心会无情地导致遗忘。格里菲斯同时加深了我们对孤独生活的同情,并惩罚了我们对永生的幻想。
格里菲斯观察到,墓碑本身“代表着一种企图——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自我讽刺的或无意识的——要求我们自己拥有有限的永恒。”V非常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有什么虚荣比它更可怜——或更辛酸和不可避免——能促使我们尝试,但失败了,决定我们被记住的术语。”
其中最丰富多彩的人物会说话的石头是出生于1795年的苏格兰妇女范妮·赖特,她年轻时“被美国自由理想的魔力迷住了”。加入美国国籍后,她毕生致力于民权事业,公开倡导废除奴隶制和争取妇女选举权。赖特试图将她的理想付诸实践,在孟菲斯以东2000英亩的林地上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社区(现在的日耳曼镇郊区就在这里)。
尽管这个名为Nashoba的社区(在奇卡索语中是“狼”的意思)未能实现其解放目标,但赖特雄辩的口才和引人注目的身材(高高的,红头发)使她成为了一个两极分化的公众人物。格里菲斯将她的故事与当代对名誉的矛盾本质和“名人的监狱”的关注联系起来。“为公众所知,”他指出,“就是为公众所拥有。即使布兰妮·斯皮尔斯获得了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也只有在狗仔队拍下她的胯下镜头后,这条消息才会出现在她的讣告上。”
 这本合集充满了流行文化的参考,将吸引格里菲斯的X世代读者。斯莫基和强盗,这是脊椎穿刺邦乔维(Bon Jovi)为作者的思考提供了试金石。其中一章“乔纳森·西里的六度”(Six Degrees of Jonathan Cilley)读起来像是凯文·贝肯(Kevin Bacon)游戏的变体。不过,格里菲斯从快速眼动阶段的即兴表演转向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的语录。这些从喜剧到哲学的转变似乎从不刺耳;它们与作者的观察相一致,死亡,就像凯文·培根的六度,是伟大的平等者。格里菲斯在书中写道:“当以前高低之间明亮的界限变得模糊、模糊,甚至完全消失时,人们很难坚持社会优越的观念。”
这本合集充满了流行文化的参考,将吸引格里菲斯的X世代读者。斯莫基和强盗,这是脊椎穿刺邦乔维(Bon Jovi)为作者的思考提供了试金石。其中一章“乔纳森·西里的六度”(Six Degrees of Jonathan Cilley)读起来像是凯文·贝肯(Kevin Bacon)游戏的变体。不过,格里菲斯从快速眼动阶段的即兴表演转向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的语录。这些从喜剧到哲学的转变似乎从不刺耳;它们与作者的观察相一致,死亡,就像凯文·培根的六度,是伟大的平等者。格里菲斯在书中写道:“当以前高低之间明亮的界限变得模糊、模糊,甚至完全消失时,人们很难坚持社会优越的观念。”
格里菲斯是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创意写作教授,也是塞瓦尼文学院(Sewanee School of Letters)的讲师,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捕捉到存在的非线性和偶然性。进步是一种幻觉,是对一系列事件的追溯标签。格里菲斯断言:“我们是可怜的、有叉的动物,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种不成熟、倒退和绕行的状态中。”他把自己在墓碑间徘徊寻找故事的方法比作“狂想曲法,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包括随意翻开一份诗歌手稿。”他称自己的方法为“墓地漫步浪漫”,一种由“动力和意外”驱动的叙事形式。
格里菲斯的联想散文以弹球机的速度和矢量重定向移动。在1880年,辛辛那提是美国“最醉心的”城市,他关于辛辛那提饮酒的那一章,从朋友们在酒吧里爬来爬去(“一种严格的、学术上合法的研究技术,我们称之为本德”),到禁酒运动,再到豆袋的发明。
把这些文章联系在一起的品质是“自传的持久链”——也就是说,格里菲斯自己的感受力,是经过几十年作家观察磨练出来的。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忘我的人”,一个“自我牺牲”的人。格里菲斯让我们注意到那些被遗忘的劳动者(“编辑、翻译、单亲父母、维修队、篮球场上的防守终结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正走向历史的垃圾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就在会说话的石头在格里菲斯的笔下,如此严肃的观察结果似乎成了值得庆祝的理由。
他诙谐幽默的技巧使格里菲斯能够处理严肃的问题——尤其是辛辛那提市种族暴力事件的反复发生——而不是屈服于绝望。格里菲斯不断地回到斯普林·格罗夫的教训上:“永生是反复无常的,是变形者,如果我们足够幸运,谁也猜不到我们的遗产会是什么。”如果我们非常幸运,我们的故事将由迈克尔·格里菲斯(Michael Griffith)这样的人讲述,他拥有洞察力和人性,能在我们的缺点和弱点之下,发现我们凡人行为中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

肖恩·金奇在奥斯汀长大,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他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现在在纳什维尔的蒙哥马利·贝尔学院教英语。
标记:伟德国际官网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