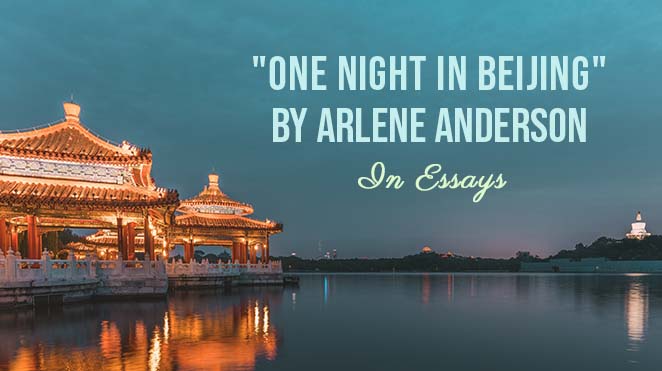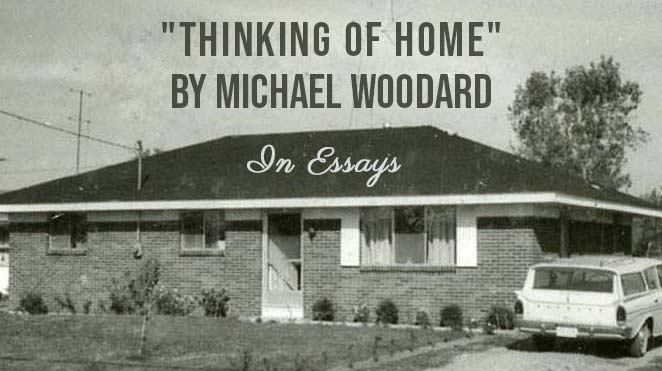他站起来,疲惫地吃力地向前走去。在西边,太阳已经落山,最后的遗迹在彩色的红色和橙色中闪耀,一缕缕淡紫色的云已经暗淡成烟灰色。夜幕已经降临在西边的某个地方,他继续朝那个地方走去,仿佛他和黑暗有什么约定。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能听到声音,鸟儿平静的叫声,一辆卡车在某个地方使劲地转动齿轮。
耶茨醒来时感觉很轻眼皮上笼罩着朦胧的颜色,热气压在他脸上和喉咙的肉上。他觉得自己的喉咙好像被一把生锈的小刀割破了,他想去摸摸看,但出于某种老掉牙的谨慎,他没有动手。有些事不如不知道。他认为最好还是谨慎地开始新的一天,谁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
 或背后。他静静地躺着,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在哪里,他去过哪里。前一晚的画面支离破碎,令人痛苦,是混乱的小片段。就像从老年痴呆的乡间度假中带回来的照片。他坐在一辆车里,六七个男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有女人吗?他似乎还记得香水和酒醉后的轻柔笑声。汽笛,巡洋舰灯光的收缩和舒张。骑马穿过神秘的树林,来到一个山谷,灌木丛拍打着汽车,树干令人窒息的冲击。 The protest of warped metal and a final shard of glass falling like an afterthought.
或背后。他静静地躺着,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在哪里,他去过哪里。前一晚的画面支离破碎,令人痛苦,是混乱的小片段。就像从老年痴呆的乡间度假中带回来的照片。他坐在一辆车里,六七个男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有女人吗?他似乎还记得香水和酒醉后的轻柔笑声。汽笛,巡洋舰灯光的收缩和舒张。骑马穿过神秘的树林,来到一个山谷,灌木丛拍打着汽车,树干令人窒息的冲击。 The protest of warped metal and a final shard of glass falling like an afterthought.
在树林里奔跑。一张照片上,他被冻在空中,四肢张开,嘴巴惊讶地摆出一个O形,一根伸出来的藤蔓或荆棘,也许是晒衣绳,勾住了他的下巴,他那可怕的气势把他抛向空中。后来,他听到了某种野兽的叫声,他怀疑这是一种尚未被科学识别的野兽,是一种可怕的潜鸟和山猫的混合体。“哦,天哪!”他大声说,然后立刻怀疑是否有人会听到,于是睁开眼睛看了看。
他首先看到的是太阳,他痛苦地扭开脸,看到一片草地,地平线上有茎、种子和三叶草花,就像缩小版的树木。一片蓝绿色的天空似乎是有生命的,它跳动着。他回头看了看上午10点左右那团白色的疼痛。
一块巨大的蓝色巨石似乎正从他头顶升起,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那是他的左腿伸到了空中,以一个陡峭的角度上升,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进入了他不想进入的邪恶的天空。仿佛有什么天上的野兽或不法的天使抓住他的左腿要把他赶走,发现他笨拙或不值得拥有,就离开了,或者只是停下来休息。
好吧,耶茨试探地说。
当他站起来时,他发现口袋的白色挡板翻反了,当他拍下自己的身体时,他发现自己的分数只不过是他来到这个世界时的一无所有。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他的牛仔裤袖口挂在了铁链栅栏上,就把他吊在了这里。他想,狗娘养的。我想我是在追什么东西,还是在逃避。他记得那些声音、枪声、骑手和他们的战马,仿佛被平版印在了暴风雨的天空上。他向前一小步,腿就颤动起来了。他看起来好像在用屁股爬栅栏,就像蛇用肋骨一样。就这样,他的粗斜纹布上有了足够的松弛,可以把他的腿扭出来。他向后一滚,在草地上坐了起来,两腿交叉着,双手捂着脸。
他说,主阿。一个人不应该这样生活。
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就像一个在牌局中为最后一张下牌而汗流浃背的玩家。谁知道他会发现什么。一具尸体,一个印有第一国民银行字样的帆布袋,一把刀刃上结了血的刀,一个死去的警长,手里攥着一张血淋淋的未执行的搜查令。但他所处的田野只有那种强烈的砷绿色,远处的树线,鸟儿在树线上方飞翔,就像玻璃滑梯上随机或恶性的孢子。当他站起来时,他发现口袋的白色挡板翻反了,当他拍下自己的身体时,他发现自己的分数只不过是他来到这个世界时的一无所有。只有这些破烂的牛仔裤和t恤。一只右脚鞋。但是耶茨有哲学思维,这对他很有帮助。如果你不知道你曾经拥有什么,那么当你失去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它。
他判断这条路是向南走的,因为他偶尔看到太阳在车顶上刺眼,而这是他所看到的唯一文明的迹象,他穿过白天令人震惊的炎热寂静,顺着链条栅栏朝南走去。他口渴极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水。
 当栅栏在路基处结束时,他一时的优柔寡断使他停下来。他向左看,向右看。Right被一种模糊的熟悉所触动,这种熟悉在社会记忆中是短暂的,从来没有人会在同一块地方走两次。他向左转,沿着路肩缓慢地走着,低着头,好像在寻找他在露莓藤和忍冬丛中丢失的什么东西。
当栅栏在路基处结束时,他一时的优柔寡断使他停下来。他向左看,向右看。Right被一种模糊的熟悉所触动,这种熟悉在社会记忆中是短暂的,从来没有人会在同一块地方走两次。他向左转,沿着路肩缓慢地走着,低着头,好像在寻找他在露莓藤和忍冬丛中丢失的什么东西。
每一个脚步都会给他的大脑带来电流。仿佛他的双脚一接触大地,就完成了某种古老的大地回路。他想到了小白鼠,其他小型实验动物的工作就是痛苦地关闭电路,直到它们恢复正常。他开始感到有一些天体科学家在观察他,他们从高处研究他,一步一步地观察他。这门课特别慢,他为什么不学?但是耶茨是个乐观的人,当他开始出汗后,他感觉好多了,他想如果他能找到一些水,他就能活下来。
他还没看清上面的字母,就看到了牌子,牌子后面是汽车电影院的大银幕,绿色的大地呈弧形排列,一排排的喇叭柱子立在那里,就像一些神秘的作物。在弯弯曲曲的泥土后面,一座白色的灰泥建筑从阳光下的风景中凸现出来。在那后面,蓝色的山阴下有一座白色的木屋。
一个他认为是女性的人,正故意沿着一排扬声器移动,做着某种下流的杂活,时而弯着身子,时而伸直身子,时而弯腰,时而向上,就像有人在摘棉花一样。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经过白色的建筑,朝树林里的房子走去,消失在树林里。
他现在可以看清那个牌子了。周四免费车,它说。他停了下来,困惑地研究着,也许是在寻找修改条款和细则。没有。他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往路基上吐了一团棉花。可能是有圈套,他大声说。他继续说。
他很快就上了车。它高高在上,停在一个平台上,平台的框架是用木炭油做的柱子。一条锯木厂的木材坡道从地面通向平台。耶茨走过去,透过栅栏往外看。一辆褪了色的绿色史蒂倍克车,看上去好像骑得很紧,而且没有用过。但免费就是免费,礼物的嘴是不可检查的。它大概是被推上了陡峭的斜坡。
我穷了一辈子,还没抢过银行。
他离开了路基。他拐进一条狭窄的燧石车道,经过一块写着“星Vue汽车影院”的牌子,穿过矗立在高高的柱子上的巨大银幕和一个无人值守的售票处,顺着弯弯曲曲的车道来到了灰泥建筑。
他绕着大楼走了一圈。他在找一个水龙头,但他没有找到。他觉得像火药一样干燥,像干树叶一样失重。地下湖中冰冷的黑水在他的喉咙里像冰一样疼痛。
他推开一扇铰链式的门,就像酒吧里的蝙蝠翼门一样。“嘿,进去,”他叫道。不回答。只有机器的嗡嗡声,看不见的风扇的呼啸声。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是在小卖部里,那里摆满了盒装糖果和口香糖,袋装薯片,他首先看到的是冷饮柜台和闪闪发光的镀铬配件。它巧妙的泵杆与球形换挡装置。你一个接一个地抽出分隔的纸杯,柜台下面的滑动门可以看到不锈钢箱里的小冰块。
 他学会了如何使用自动售货机,刚喝完一瓶可口可乐和半杯橙汁汽水,门就开了,一个红头发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回头看了看耶茨,直到她撞上了他。“妈的,”她说,然后睁大眼睛跳开了,橙色的苏打水洒在她的胸前。
他学会了如何使用自动售货机,刚喝完一瓶可口可乐和半杯橙汁汽水,门就开了,一个红头发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回头看了看耶茨,直到她撞上了他。“妈的,”她说,然后睁大眼睛跳开了,橙色的苏打水洒在她的胸前。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是谁?
耶茨捡起冰块,把它们放回纸杯里。他四处寻找可以擦苏打水的东西。
我刚从路上开过来。我需要喝点水。
她说:“我想如果你破产了,你就会去银行自己拿。”把口袋装好就走。
我穷了一辈子,还没抢过银行。
嗯,你还年轻,她说。给自己一点时间。没有必要匆忙做事。
耶茨把冰块放在柜台上,端详着她。她有一双明亮的绿色眼睛,苍白的皮肤上有淡淡的雀斑。一个像美杜莎一样的红色卷发被喷得很浓,似乎是上了釉,在窑里烧过的。他在她四十多岁,也许四十五岁的时候评价她。为了应付天气,她穿得很厚,都是保暖的男式服装,他看不出她的身体怎么样。
好吗?你想看看我的牙齿吗?
什么?
你把我看得跟拍卖场上的马一样。
耶茨把头移开,什么也没说。
你只是推开门走进来,就像你是这里的主人一样。我们这里打烊了。你不能在白天放电影。
我只是在找水龙头,但找不到。我去拿杯酒,然后就走。
在去哪里的路上?
我不知道。不管这条路上有什么。
你从哪里来?
他做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手势,似乎把地平线、整个世界都包围了。
你没有家人吗?
耶茨喝完橙汁饮料,用牙齿咬碎冰块。他从没见过这么小的冰块。就好像他们只是半生不熟。他一直对事物的起源感到困惑,他想知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每个人都有家人,不然我也不会在这儿,”他说。但我的家人都死了。我是个孤儿。我和一帮坏人混在一起被抢了。这些天在路上很不顺利。那辆车怎么样?
怎么了?
像招牌上写的那样免费吗?
我们在星期四晚上抽签。抽奖活动。整整一周,这些票都被放进一个盒子里,然后抽出一张。如果买彩票的人在这里,他就赢得了这辆车。
在我看来,它仍然是固定的。你得已经有车了才能赢这辆车。
不。我们有很多行尸。这是艰难的时期。很多人都没有车。
哦。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免费。
什么?
如果你必须买票来看演出的话。
这辆车是免费的。你买了电影票去看电影,说到免费,饮料就不免费了。每只15美分。
就像我说的,我被抢了。他们把我的口袋翻反了。我想我欠你15美分。他往杯子里塞了些东西,想知道她是否可以用某种化学测试来检测橙子中可口可乐的残留物,就像测谎仪测试一样。你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
我不会向一个口渴的人要价一杯冷饮。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请自来。但如果你想赚点钱,这里也有工作。
耶茨已经放弃了史蒂贝克。今天没有免费的车。
他拖着一个巨大的铝垃圾桶进了有桨的扬声器里,停下来观察地面。他们到处都是爆米花袋、可乐杯、烟盒和餐巾纸。被风吹起的纸,看起来像大风暴的碎片。他说:“每个晚上路过的狗娘养的都必须把自己的车翻出来,然后开车离开。”
但这是一项轻松容易的工作,他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沿着梯级走下去,双手捡起废料,就像一个人摘棉花一样。工作时,汗水浸湿了他的衬衫,但在这似乎有目标指引的日子里,感觉很好。他开始用口哨吹起他童年时失传的老歌。他会在垃圾桶周围巡逻,然后他会移动垃圾桶,然后重新开始。当罐子装满时,他把它倒进了小卖部后面的一个钢铁焚化炉里,点燃了它,然后回到了田里。有一次,当他把罐头倒进网筒时,她出来看看他。好吧,她告诉他,你会工作的。我来替你说。
在树林旁边的最后一层,发现的情况则是另一种性质。啤酒罐,几个半品脱的瓶子。一种薄薄的乳胶管,像咸水退潮时留下的海吸虫。爱神的名片。上帝玷污了爱的容器。我不碰那个,他大声说。他蹲在地上想这件事。他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是什么。他想知道她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他应该去问她吗? How to phrase it. He couldn’t think of a delicate way to put it, and perhaps it had never happened before. As so often it was of no moment. At length, he rose and caught it up on a length of a stick and carried it out to the garbage can, holding his arm stiffly extended and slightly to the side as if germs were blowing off it.
 当最后一份文件被烧掉时,他在阴暗的寂静中坐在小卖部后面,静静地听着白天的动静。每一个声音似乎都是独立的,独特的,独立的,每一个声音似乎都有超越自身的意义,好像每一个声音都代表着什么。一辆卡车在远处看不见的路上驶过。鸽子从房子后面的树林里叫着,温柔而悲伤,好像它们有什么损失要向他哀悼。他抬起头来。天空万里无云,湛蓝无底,鸟儿在风中飞舞,就像解了绳的黑色小风筝。他站起来走了进去,告诉她他吃完了。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内心平静。
当最后一份文件被烧掉时,他在阴暗的寂静中坐在小卖部后面,静静地听着白天的动静。每一个声音似乎都是独立的,独特的,独立的,每一个声音似乎都有超越自身的意义,好像每一个声音都代表着什么。一辆卡车在远处看不见的路上驶过。鸽子从房子后面的树林里叫着,温柔而悲伤,好像它们有什么损失要向他哀悼。他抬起头来。天空万里无云,湛蓝无底,鸟儿在风中飞舞,就像解了绳的黑色小风筝。他站起来走了进去,告诉她他吃完了。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内心平静。
放映员在黑暗的卡座里展示了加里·库珀(Gary Cooper)的西部片,片中一个男人背靠墙壁,最终站了起来。对耶茨来说,摆弄着嗡嗡作响的机器的放映员是一个苦于配制魔药的炼金术士。就好像是他编造了这个寓言,从某种集体无意识中破译出来的。耶茨从未见过顽强的个人主义得到如此大的回报,却遭到如此巧妙的挫败。他看着放映员在一卷一卷的放映机之间切换,学会了注意画面右上角的那个白色圆圈,那是放映机结束的信号:从此以后,他会想象这对他来说像是上天指引的信号,他会知道他所处的那个放映机即将结束,他会想,该走了,该叠牌了,该走了。开始另一个节目。
灯亮了,最后一辆车开走了很久之后,他仍然被他看过的那出戏惊呆了。就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他得到了加里·库珀这个朋友,一个熟悉的坚忍的黑人和白人,当事情变得艰难时,他会站在他身边。
你喜欢他妻子最终击毙最后一个逃犯的那部分吗?他问道。
我看过太多次了,女人说。我总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再也不喜欢电影了。坏人总是中枪,好人总是得到女孩。它从来没有显示过之后会发生什么。
她的名字叫威洛丁·罗斯,他知道她来自密歇根。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问。
她说:“我丈夫在找一个理想的地方喝个烂醉。”他觉得这是个完美的地方。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她在清理烤架,耶茨在清理烟头和被踩坏的可乐杯。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经营好这个地方的,”他说。卖票什么的。做了一晚上的汉堡什么的。我们俩都快死了
她说,几天前我还有个帮手。她正在清空收银机里的钱,把钱装进一个白色的帆布袋里。
他为什么辞职。
他没有放弃。我炒了他。
如何来。看来你需要帮助。
“我不需要那种帮助,”她说。他知道我是个寡妇他认为这给了他占我便宜的借口。
嗯,耶茨说。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一直在无所事事地思考今晚该睡在哪里,现在他猜这句话告诉了他他不在哪里。
最后他睡在小卖部的躺椅上。她从房子里拿来毯子和枕头。后面的浴室里有个淋浴,她告诉他。我不想针对你个人,但我相信你能忍受。我想在路上的卫生是不一样的。
她走后,他不慌不忙地检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后面的房间里有个冷冻室。他打开门,冷空气冒了出来。一袋袋的冷冻汉堡,一捆捆整齐的香肠捆在塑料石棺里。他从未见过如此慷慨。在另一个房间里,一层层装在纸箱里的糖果,每个都用玻璃纸包装着。如此容易接近,你所要做的就是撕掉纸。可乐机是用之不竭的,就像某首老歌里唱的柠檬水之春那样。
他吃了三个剩下的热狗和一袋薯片,然后他吃了一块糖果,喝了一杯樱桃可乐。他环顾四周。好了,他说。他非常满足,他是自己领域的主人,是他所考察的一切的主宰。他一直在无所事事地想着那些渴望爱情的寡妇和孤独的伤痕累累的流浪汉,但这些在这里似乎不再适用了。最后他整理好自己的床,爬进去盖上被子。他躺了一会儿,惊叹于生活的曲折和逆转,它可以带你进行奇怪的旅行。就在今天早上,他醒来时身无分文,连下一顿饭都前途渺茫。现在他心满意足,成了一家兴旺企业的半老板。他躺了一会儿,试图编造一个计划,在汽车的图纸上造假。 An accomplice perhaps, raising aloft the ticket Yates had slipped him. That’s me, the accomplice cried, that’s my number.
但是这一天实在太满了,他感到非常疲倦。制冰机发出令人安慰的嗡嗡声。他闭上了眼睛。当他半睡半醒地睁开眼睛时,他想象着自己的头靠在一个马鞍的骨头上,天花板上缀满了星星,库普从即将熄灭的营火里用困惑而宽容的眼睛看着他。
版权(c) 2013年由威廉·盖伊遗产管理公司。版权所有。这个故事是在盖伊的手稿中发现的,在这里忠实地复制,没有重大编辑。阅读米兰向威廉·盖伊致敬,包括达内尔·阿努特、阿德里安·布莱文斯、桑尼·布鲁尔、托尼·厄利、罗伯特·希克斯、德里克·希尔、苏珊娜·金斯伯里、兰迪·麦金、因曼·梅杰斯、科里·梅斯勒、克莱·里森、乔治·辛格尔顿、布拉德·沃森和史蒂夫·亚伯勒的文章,请点击在这里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盖伊的一次采访,以及他去世时正在创作的小说的两段节选。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