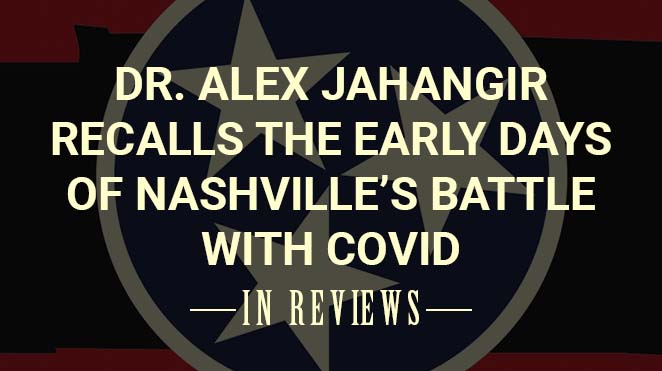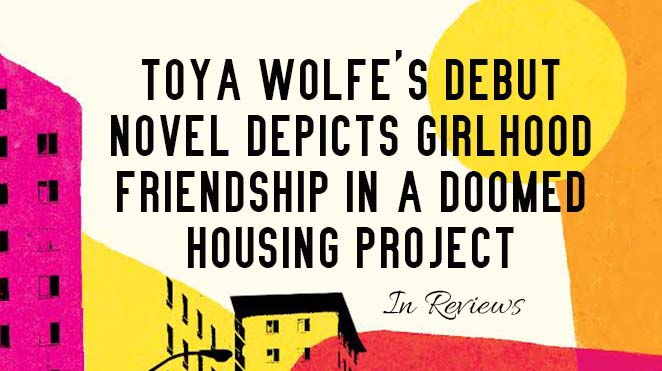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1949年的一篇题为《文化批评与社会》的文章中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认为,大屠杀的恐怖扼杀了人类通过艺术进步的可能性,使美的慰藉变得空洞。如果创造了歌德和Hölderlin的文化也能把六百万无辜的人送进毒气室,我们又怎能不带着讽刺转向文学呢?其他作家则坚持认为,所有试图通过散文表现大屠杀暴行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为语言根本无法再现这种暴行的规模。
 这些众所周知的论点必然会放大吉姆·谢泼德摆在自己面前的艰巨任务亚伦记这部小说从一个贫穷的犹太男孩的视角出发,在著名作家、儿科医生和孤儿院主任雅努斯·科尔扎克(Janus Korczak)的帮助下,他试图在华沙犹太区生存下来。科尔扎克拒绝了无数次让他自由地与他照管的孤儿呆在一起的提议,并在1942年孤儿被驱逐到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时拒绝抛弃他们。
这些众所周知的论点必然会放大吉姆·谢泼德摆在自己面前的艰巨任务亚伦记这部小说从一个贫穷的犹太男孩的视角出发,在著名作家、儿科医生和孤儿院主任雅努斯·科尔扎克(Janus Korczak)的帮助下,他试图在华沙犹太区生存下来。科尔扎克拒绝了无数次让他自由地与他照管的孤儿呆在一起的提议,并在1942年孤儿被驱逐到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时拒绝抛弃他们。
谢泼德显然明白他的任务的严重性:亚伦记书的结尾是一份六页纸的资料清单,开头是玛格丽特·尤森纳尔的一段话,表达了我的目的:“我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通过仔细检查文件本身所提供的内容,来接近内在的现实。’”尽管(或者也许是因为)传奇人物科尔扎克博士留下了大量关于他的作品,但谢博德把他作为一个次要角色,用早熟的阿伦(Aron)的口吻来写作,后者是科尔扎克照顾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想象的例子,所有这些孩子都在特雷布林卡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之前失去了家人。
这是一个有趣的叙事选择亚伦记大屠杀题材的独特变体。在埃利·维尔瑟尔晚上和安妮·弗兰克的《一个小女孩的日记在美国,我们看到受过教育、富裕的家庭逐渐陷入贫困,被剥夺财产和尊严,最终被送进死亡集中营。但从一开始,阿隆基本上是穷困潦倒的,这一地位使他对苦难有了独特的看法。即使没有德国人的到来,世界可能也不会原谅阿隆。但德国人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惧、饥饿和死亡。利用街头顽童的生存本能和逃脱麻烦的诀窍,阿伦与一群男孩和女孩组成了团队,他们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从贫民区内外走私食物和补给,以维持他们的家人的生存。“偷东西总是不对的,”阿伦的妈妈说。“饥饿总是错误的,”他反驳道。
 “我的父母给我起名叫阿伦,但我的父亲说他们应该叫我‘你做了什么’,我的叔叔告诉所有人他们应该叫我‘你在想什么’,”谢泼德在小说的开头写道。开头这句话的幽默语气贯穿始终亚伦记,通常以黑色幽默的形式,以某种方式放大而不是减少可怕的情况。后来,德国人占领了华沙,把那里的犹太人赶进了拥挤的贫民区,阿隆和另一个男孩在走私一袋萝卜时被抓。他们在一间名为“街车”的等候室里等待时,男孩开玩笑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他穿了一件红色的束腰外衣以防受伤,而希特勒则穿了一条棕色的裤子。”过了一会儿,一名德国士兵进入电车,朝男孩的头部开枪。
“我的父母给我起名叫阿伦,但我的父亲说他们应该叫我‘你做了什么’,我的叔叔告诉所有人他们应该叫我‘你在想什么’,”谢泼德在小说的开头写道。开头这句话的幽默语气贯穿始终亚伦记,通常以黑色幽默的形式,以某种方式放大而不是减少可怕的情况。后来,德国人占领了华沙,把那里的犹太人赶进了拥挤的贫民区,阿隆和另一个男孩在走私一袋萝卜时被抓。他们在一间名为“街车”的等候室里等待时,男孩开玩笑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他穿了一件红色的束腰外衣以防受伤,而希特勒则穿了一条棕色的裤子。”过了一会儿,一名德国士兵进入电车,朝男孩的头部开枪。
当阿伦最终与家人分离,找到雅努斯·科尔扎克时,小说的基调有所提升,因为科尔扎克对孤儿的奉献,以及拯救他们生命和精神的不懈决心,不禁让人受到鼓舞。科尔扎克喂养孩子们,照顾他们的疾病,但他也鼓励他们唱歌和表演戏剧。此外,在他们都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之后,他拒绝抛弃他们。尽管阿隆的声音直率而不带感情色彩,但毫无疑问,我们是想把他的韧性和科尔扎克的同情心作为面对恐怖的真正英雄主义的例子。
为什么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旧的恐怖故事呢?有人说,我们需要它们来纪念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人类能够达到的深度,这样我们就不会陷入同样难以言表的罪恶。我怀疑小说像亚伦记它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它们提醒我们,这种邪恶,即使以其最亵渎、最顽强、最不可理解的形式,也永远无法完全战胜我们。当然,我们有生存的意志,但我们也有爱的能力和为了我们所爱的人而坚持下去的毅力,即使面对必然的死亡。Janus Korczak告诉Aron:“虽然事情已经非常糟糕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行动是无用的。”与亚伦记吉姆·谢泼德(Jim Shepard)交出了一部既令人震惊又振奋人心的小说,我怀疑它注定会成为它致敬的遗产的一部分。

埃德·塔金顿(Ed Tarkington)拥有弗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的学士学位、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硕士学位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创意写作项目的博士学位。他的首部小说,只有爱才能让你心碎,将于2016年1月由Algonquin Books出版。他住在纳什维尔。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