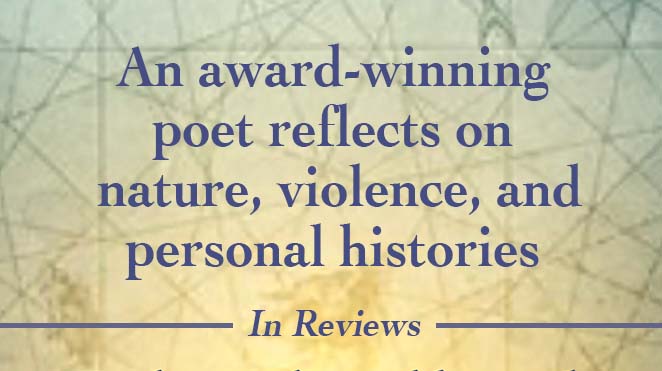罗伯特·帕尔默是一位音乐家的音乐评论家。尽管他偶尔会出言不逊(比如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角色是“精心设计的”和“矫情的”),但他还是受到了许多表演者的钦佩,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流行音乐的非凡了解。波诺称帕尔默为美国音乐界的“übertutor”,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提到了他的博学:“他会向你介绍各种新事物和旧事物——他非常熟悉这些事物。”但是帕尔默在他的工作中带来的不仅仅是智慧。蓝调与混乱这本书收集了帕尔默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7年去世的作品,揭示了他为什么能够以崇高评论家的身份发表评论《纽约时报》而且《滚石》杂志但仍能在众多艺术家中保持信誉和好感。很简单,他喜欢他们创作的音乐,他狂热地相信音乐的重要性。
像大多数写音乐文章的人一样,帕尔默自己也是一名音乐家,他是一名单簧管和萨克斯管演奏家,在60年代末与一个名为昆虫信托(Insect Trust)的迷幻融合乐队录制了几张专辑。70年代中期,他将注意力主要转向写作,成为《纽约时报》的首席流行音乐评论家次但多年来,他继续断断续续地演奏,在20世纪90年代,他为密西西比的Fat Possum厂牌制作了布鲁斯唱片。
出生于阿肯色州的帕尔默对蓝调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作为评论家,他涉猎广泛,从纽约朋克到摩洛哥G’naoua音乐,他是公认的南方布鲁斯的权威,他认为南方布鲁斯是20世纪流行音乐的源泉。他1981年出版的书,深蓝,对于任何对这一类型感兴趣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关键文本。1988年,他离开纽约回到南方,在孟菲斯和新奥尔良度过了一段时间,提拔了一些不知名的蓝调艺术家,合作了一些关于蓝调和摇滚的纪录片,并在密西西比大学(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教授民族音乐学。与此同时,他一直在写作,经常是为了《滚石》杂志.
帕尔默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评论,以及相当数量的录音笔记。蓝调与混乱这不是他的作品的全面收集,而是一个跨越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兴趣范围的选择。编辑安东尼·迪库蒂斯(Anthony DeCurtis)按主题组织了选集,让读者从多个角度体验帕尔默对一个主题的看法。例如,专门介绍蓝调的部分包括帕尔默1978年对浑水的经典特写《滚石》杂志;内页注释整夜, 1993年Junior Kimbrough & the Soul Blues Boys的CD;还有他最后的作品之一,《为什么我戴着我的魔咒手》,这是一篇简短,神秘,有趣的文章牛津美国人.藏品中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作品,包括对威廉·巴勒斯的长篇采访,但从整体来看,蓝调与混乱是对二十世纪晚期美国音乐的内部调查。
帕尔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似乎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但他的天赋在他的艺术家简介中尤其明显。他有一种技巧,可以传达一些相当古怪的人物的天才,他成功地用他的散文飞得很高,同时仍然做扎实的报道。在1972年的一篇关于爵士乐创新者奥内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的文章中,帕尔默将科尔曼的对话风格与他的音乐进行了比较,他写道,科尔曼的对话风格“体现了相同的思维模式,围绕主题旋转,远离主题,在你最不期待的时候回到起点,然后再次离开,随着感受和想法的变化而进步,像矮胖子一样平衡在虚空的边缘,空间和时间中间的洞。”然后,他把文章的一大块内容交给科尔曼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让他可以不间断地长篇大论。
帕尔默似乎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一步,让他的主题说话。他1979年《滚石》杂志在《魔鬼和杰里·李·刘易斯》一开始,刘易斯就滔滔不绝地说:“我是最坚强的狗娘养的,从一个肉屁股里拉出来的。”没有一个记者的聪明言语能更好地介绍刘易斯的浮夸和自我厌恶的独特结合。
尽管帕尔默擅长捕捉音乐世界的个性,但他或许更擅长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探索音乐的技术层面。无论是解释模态爵士乐还是讨论印度音乐的音调细微差别,帕尔默都保持简单。在这里,他准确地描述了Muddy Waters是如何超越布鲁斯的基本结构来创造出他的声音:“但是如果你仔细听Muddy,或者其他真正深沉的布鲁斯歌手,你会发现他系统地唱出了音阶的第三个音符,特别是第五个音符,这取决于音高落在哪里,以及他试图传达的情感。”
如果有一个元素贯穿于帕尔默的所有作品,那就是对他所写的音乐文化重要性的坚定信念。他从不为自己是流行音乐的评论家而道歉,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仅次于欧洲古典传统的第二名。尤其是布鲁斯,他形容为“神圣的”,他的意思是,这种音乐在精神上和感官上都能打动听众,是一种超越的方式。这种灵魂的激荡似乎正是帕尔默在他所有的音乐探索中所寻求的。1997年,迈尔斯·戴维斯的经典曲目再次发行有点蓝,帕尔默写道,“如果我们在一生中一次又一次地听它——嗯,也许那是因为我们感觉还有一些东西更多的,还没有听到。或者我们只是喜欢定期去天堂。”这句话可能是他的信条。
标记:非小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