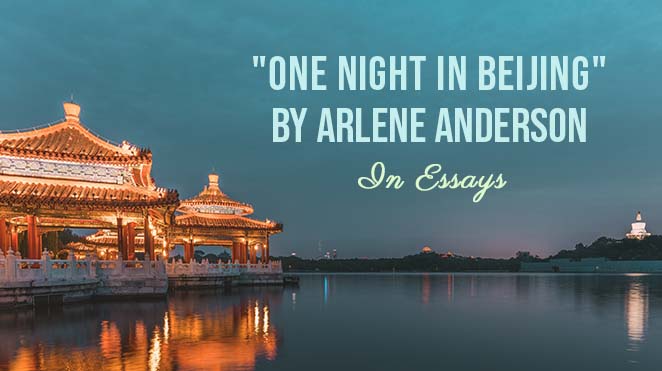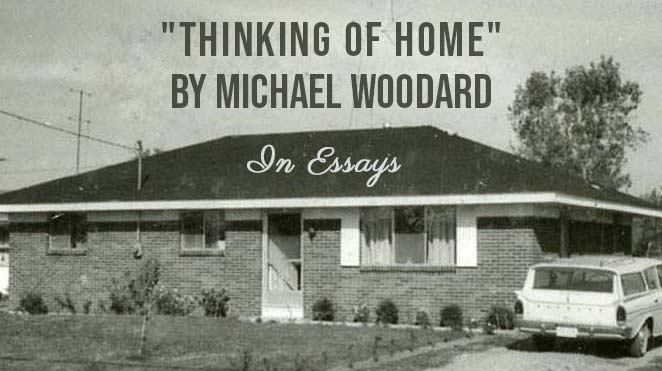法院判给她摩托车的监护权,他们今天要去取。当白色福特敞篷车从拐角处开过来时,边水坐在路边喝着硬纸板箱里的橙汁。一顶维多利亚皇冠,顶朝下,尽管那天很凉爽,而边水镇一直坐在太阳下,因为天气太热了。那辆汽车拖着一辆他认为是拖车的东西。
 克莱尔慢慢地把车开到路边,把它推到停车场,让它空转。她脏兮兮的金发上围着围巾,神情有点夸张。当她用鲜红的指甲把墨镜往上一推时,她的眼睛是虹膜的颜色。
克莱尔慢慢地把车开到路边,把它推到停车场,让它空转。她脏兮兮的金发上围着围巾,神情有点夸张。当她用鲜红的指甲把墨镜往上一推时,她的眼睛是虹膜的颜色。
你来这里做什么,水手?
只是在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出现,他说。
准备好了吗?
他进了车,砰的一声关上门。我准备好了。
这是田纳西州的孟菲斯,1952年4月中旬,敞篷车已经在滚动,被冲洗掉的阳光像发光的水一样洒在店面的玻璃上。她开着车,穿过一条小巷,进入一个日益衰败的社区。在那里,酒徒和街上的流浪汉似乎被这再生的阳光吓呆了,他们不习惯这样充足的阳光,所以他们朝胡同里走去,好像长时间的暴晒会把他们烤焦或烧焦他们的衣服似的。酒吧和酒店在这些狭窄的街道上争抢空间,两者似乎都有很好的代表性。他们一副茫然的样子,他们那卷死气沉沉的霓虹灯作品正等着夜幕降临。
她瞥了他一眼。
“天哪,我讨厌你的穿着,”她说。我得给你买几件衣服。
埃奇沃特穿着一件海军粗布衬衫和牛仔裤,用一根带扣的带子系着,上面写着美国海军。我没事,他说。
听。在这件事上你得耐心听我说。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持住,好吗?
等一下。那是什么意思,不管发生什么?我以为我们只是来取你的摩托车。
嗯,你知道的。毕竟,他们是我的亲家。可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感觉。
这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豪宅,除了模糊的记忆,没有什么丰裕的痕迹。在低垂的榆树下,叮当作响的汽车正在康复或死亡。树荫树机械师盯着他们的马达,好像他们会用纯粹的意志使他们复活,或者用忠实的治疗者的电手把他们从死亡中复活。
经过一栋破旧的红瓦屋顶的蓝色豪宅时,她停了下来,嘴角叼着一根烟,向后看了看。她剪断方向盘,熟练地把车倒在人行道上,开上了一条柳树低垂的车道。
表演时间到了,她说。
抛光的镀铬和光滑的黑色皮革,摩托车似乎在等待春天,在后院设置了陌生和未来。
克莱尔下了车,砰的一声关上门。边水紧随其后,慢慢爬出汽车,就像一个人小心翼翼地进入冰冷的深水。在拖车的床上有几根2乘8的木板,他把它们排成一个临时的斜坡,转向倚在支架上的哈雷戴维森。
她说:“把一个妓女的手放在摩托车上,你就会缩回一根血淋漓的屁股。”
一扇纱门松垮垮地贴在门框上。一个身材矮胖的女人来到后门廊,她迈着毫无意义的步伐快速地穿过门廊,并期待地摩挲着双手。她说:“把一个妓女的手放在摩托车上,你就会缩回一根血淋漓的屁股。”
快点,克莱尔说。
他刚举起支架,把前轮转向斜坡,那个女人就开始尖叫起来。你毁了我儿子的生活,婊子,她吼道。她一步两级地走下台阶,克莱尔转过身来,试着走了一步,但那个女人像风暴锋面一样无情地紧紧抓住她,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然后一只手放在克莱尔的肩膀上,把她扔到草地上,倒在她身上。
该死,边水说。
他把摩托车开到坡道一半的时候,纱门又砰地一声响了起来,一个穿着破旧灰色汗衫的男人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支未上膛的双管猎枪,摸索着往里面装上蜡的红色汽缸。他掉了一个,正在地板上乱摸。
当埃奇沃特听到枪管拍打的声音时,他已经把自行车从斜坡上滚了下来,跨在上面,启动它,他已经在滚动了,这时脑震荡就像打在头上一样。他穿过像迎风飘起的绿雪一样旋转的碎草木,盲目地滑到街上,然后在他控制住摩托车之前,穿过了一处树篱,又回到了街上。他迎着风,两边的房子像万花筒一样从他身边经过,就像他被弹射过去的俗艳隧道的墙壁。
影像中的街道从后视镜里滚进滚出,然后白色的福特出现了,并以平静的步伐跟在后面。边水放慢了速度,把摩托车开进了一家酒店的停车场,她在旁边转弯。那辆哈雷车就像一头凶猛的野兽,连呼吸都不急促。她在笑。
我的混蛋,埃奇沃特说。
你相信吗?我姐夫不得不跑出去和他争抢枪。他把那棵树打得屁滚尿流,你看到了吗?
“我骑马穿过了它,”边水说。
“啊,宝贝,你的头发上都是,”她说着,用手把头发梳开。
他们不得不费力地把自行车搬到拖车上,因为她认为停车取木板不明智,埃奇沃特用她带来的绳子把自行车竖直地捆在一个支撑物上。
这是我第二次在这里和这个沉重的狗娘养的摔跤了,他说。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你心情不错,”她笑嘻嘻地说,上了车。
“我真的不喜欢挨枪子儿。”
她慢慢地把车开到街上,向北驶去,从后视镜里看了看自行车是否安全。“今晚你会感觉好些的,”她说。我们会找个地方给你买件运动外套,然后去一家很好的餐厅。也许是意大利菜,我们去喝一瓶好酒。好吗?
好吧,埃奇沃特说。
这位潜在的摩托车买家住在孟菲斯东部一个叫莱顿的小镇上,他们驱车前往那里,经过了大片的房屋和公寓大楼,来到了平坦的乡村,那里有房屋拖车和被拖拉机包围的农田,埃奇沃特看着这些拖拉机在似乎无边无际的棉花地里无声地移动。
在他认识她的短暂时间里,她似乎总是扮演着某种角色。一个人很少会重复一次。就是今天那部电影的明星。他有一种冲动,想环顾四周,看看电影摄像机在嗡嗡作响,一个化妆师带着他的药水准备好了。
他转过身来,对着滑动的风景端详着她。她的右眼眼角有一处淡淡的蓝色瘀伤,脸颊上有一道划痕,但风吹着她的头发,丝巾在微风中飘荡,她看上去很放荡,对自己很满意。在他认识她的短暂时间里,她似乎总是扮演着某种角色。一个人很少会重复一次。就是今天那部电影的明星。他有一种冲动,想环顾四周,看看电影摄像机在嗡嗡作响,一个化妆师带着他的药水准备好了。
当他看着她时,她的侧影似乎改变了。肉开始烧了,融化了,从头盖骨上掉下来,顺着她穿的亚麻罩衫往下掉,亚麻布本身也变黑了,腐烂了,风把它的碎布卷走了。当她转过身来,用那只抓着方向盘的瘦骨嶙峋的手对他咧嘴笑时,她头盖骨上空洞的眼窝冒着烟,像一片烧焦的风景,远处有微弱的黄光闪烁着,熄灭了。她咧着嘴笑的牙齿在牙窝里松动了,右边的犬齿与下颌骨相连的地方有一个发黑的洞。
他们来到一座白色的灰泥建筑前,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灯泡框起的福斯塔夫啤酒招牌。卡洛琳广场,牌子上写着。
边水说,停在那儿。
什么?
让我在这儿等你。我得打个电话。
她已经开始放慢脚步了,但她还是转过身来对他皱起了眉头。她说,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快到雷顿了。你可以在那里打电话。再说了,你会打给谁?你谁都不认识。
他几乎在车停下来之前就出来了。你办好生意后来接我。我在里面喝杯啤酒。
她瞥了一眼牌子。“只要你他妈的别碰卡洛琳,”她说。
边水穿过一个白色的停车场,停车场里满是粉碎的贻贝壳。卡洛琳广场坐落在地球上,几乎没有树木和灌木,粉刷成灰泥的小酒馆似乎已经吸收了方圆几英里内的所有营养。周六晚上在现场音乐的伴奏下跳舞,窗户上的海报上写着,但边水已经被一种日益高涨的绝望所感动,他向自己保证,周六晚上他会在其他地方跳舞。
他走进了一种阴冷的阴暗环境,里面弥漫着酒花和香烟的气味,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被一种几乎是幽冥的寂静所触动。一个坐在吧台边的男人看着他穿过房间。埃奇沃特的眼睛里仍然充满了外面四月的阳光,他走进的房间就像一个洞穴,酒徒们坐在桌子旁,他们暂时放下了他们的镐,从他们的劳作中休息一下。
给我来一杯,他对酒保说。他从牛仔裤的手表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钞票。酒保用水龙头盛满一个磨砂的杯子,把泡沫耙进一个开槽的槽里,然后把啤酒从柜台上滑过。酒保一头上了凡士林的红头发,分在中间,满脸雀斑,手指上有褐色斑点,像香肠一样。
边水喝了一大口啤酒,点了根烟,坐在那里享受着寂静。就连酒桌上的饮酒者也很安静,似乎还在想着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他能感觉到寂静就像他给自己画的安慰,他很高兴克莱尔和摩托车正在远离他的某个地方滚动。
卡洛琳广场坐落在地球上,几乎没有树木和灌木,粉刷成灰泥的小酒馆似乎已经吸收了方圆几英里内的所有营养。
克莱尔有些紧张不安,无法平静下来。她总是在动,总是在说。他看着她睡着了,但她的生活还在继续,她的脸在嘴角紧张地抽搐着,她那虹膜色的眼睛在半透明的眼皮下转动,像湍急的蓝色海水。她的四肢不安地颤动着,他认为即使是她的梦也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梦更明亮、更响亮、更快。看着她熟睡的样子,他觉得自己偷了一件不想要却又无法归还的东西。
他感到有人在盯着他,便抬起头来。隔着两条凳子的那个人在看着他。他身材魁梧,穿着工装裤,猪一样的小眼睛醉醺醺地盯着边水镇。他似乎在努力回忆他在哪里见过边水镇或者像他这样的人。他做了一个酒保几乎听不懂的手势,酒保从冷藏箱里拿出一只滴滴答答的棕色瓶子,打开放在那人面前,然后用类似仪式的东西给他的酒杯斟满了酒。
你在看什么?那人问艾克沃特。
“没什么,”边水说。他移开视线,看着一排排绿瓶子后面的镜子。在摇摇晃晃的镜子里,他的倒影又暗又细,扭曲着。
他拿起三张一美元纸币,从吧台那边滑过。“给我些零钱打电话,”他说。
你参加过战争吗?楼下的人问他。
边水想起了猎枪的震荡声和飘散的柳叶碎片。他说,不是在任何一个正式的地方。
零钱在吧台上嘎嘎作响。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把零钱掏出来,捧在手心,经过一个无声的自动点唱机,走到挂着电话的后墙上。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似乎对它的功能和操作方式感到困惑,他手里的拳头硬币沉重,他能感觉到腋窝里有汗,冷冷的顺着胸腔往下流。他转过身,穿过一扇写着“男人”的门,在一个褪色的水槽里小便,在水池边洗手洗脸,然后用从金属容器里解开的一段布料擦干身子。水池上面没有镜子,在原来镜子的地方只有四个支架。在灰泥上,一个人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你看起来很好。
他走出去,用了电话,听到铃声响起,此刻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然而,电话铃响个不停的那个房间在他的脑海里是真实的,他茫然地想,如果他们把客厅的墙壁刷了漆,会不会少了什么东西,或者增加了什么东西。
最后,一个年轻女子接了电话。水滨的妹妹。
我几乎要放弃你了,埃奇沃特说。
比利?是你吗?你到底在哪里?
他怎么样?
上次你打电话时我说的就是他。他的死亡。你怎么没来?
“我在路上,”他说。我会去的。我遇到了一点坏运气。
她认识他,她甚至不想知道细节。“你最好到这儿来,”她说。他一定要见你。必须。他想纠正错误。他想撑到你来。
他这么说的?他说他想撑到我到那儿?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该说出来的,”她告诉他。或者应该这样做。你想在你的造物主带着这些东西之前离开吗?
埃奇沃特说:“我不期待它带着它,也不期待它空手而归。”
好。你和你的小嘴。
我得走了,埃奇沃特说。
“你有毛病,”她说。如果你不是那么
他悄悄地断开了连接,抱着电话。然后他又拿起话筒,凑近耳朵,发现只有拨号音,这似乎是个奇迹。没有好消息或坏消息,只有单调的单音电子嗡嗡声,没有来源,但在他周围,永恒的嗡嗡声,无论什么力量的世界慢慢减少。他重新拨动了电话。
酒吧里的那个人转了转凳子看边水,边水看到了他在别人脸上的表情,他想:去他的。他拿起啤酒和剩下的零钱,走到酒吧的角落里。
“你没穿制服。”那人在他身后喊道。
“我出院了。”我不是军人。
那人挣扎着从凳子上站起来,喝干了酒杯里的酒,打开酒杯喝了下去,喉结断断续续地抽动着。他把瓶子往后一放,笨重地朝边水镇走去,活像一只优雅的跳舞熊。边水想要一根球杆,一双有魔法翅膀的鞋子。一辆摩托车。
不管你穿不穿,你都不尊重制服。这是海军工作服,别以为我不认识。我在战争期间穿的所有衣服。你穿着他们的衣服,甚至都没被遮住。
“我出院了,”边水特小心翼翼地说,竭力想说清楚。在加州长滩。我出去了。我服了四年兵役,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他拿起杯子和香烟。他把幸运牌装进口袋,向吧台上方走去。“让我再喝一杯,”他说。
别惹埃德,酒保说。他是个坏消息。
他绝对是,埃奇沃特说。但我希望是给别人的。
边角水能闻到他的气味,看到他皮肤上坑坑洼洼的毛孔,鼻子里的静脉就像细小的爆炸断层线,感觉到他愤怒的脓漏呼吸。
你们这些混蛋呢?男人问。他又走近了,身子前倾到边水镇的脸上。边角水能闻到他的气味,看到他皮肤上坑坑洼洼的毛孔,鼻子里的静脉就像细小的爆炸断层线,感觉到他愤怒的脓漏呼吸。
当我在大洋彼岸打仗,战死沙场的时候你们这些混蛋却在这里喝光了我们所有的威士忌,上了我们的老婆。那个怎么样?
地狱火。埃奇沃特说。我还没到那场战争的年龄。你能不能别来烦我?
为你们这些混蛋战斗牺牲。我有勋章可以证明。
来杯啤酒怎么样,埃奇沃特说。
“也许你应该把酒喝光,然后走开,”酒保说。他的头像一顶金属帽一样闪闪发光。你不是这里的常客。
“我可能会成为一个,”边水说。
但你也可能不会。
“你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有意识的反对者之一,”埃德说。
边水把杯子里的水倒干,轻轻地放在吧台上。他转身要走,但还没迈出第一步,就有一只沉重的手抓住了他的衬衫领子,用力一拉,他感到扣子弹开了,衬衫从后面扯了下来。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他猛地转过身,抓住杯子,狠狠地砸在艾德的脑门上。它甚至没有折断,当他有点惊讶地看着它时,酒吧老板不屑用正常的接近方式,用一根长得很重的锯木球杆跨过吧台,狠狠地在边水的左耳上方拍了一下。边水的膝盖碰到了水,他瘫在了地板上。世界先是光明,然后是黑暗。
有人踢了他一脚,一阵恶心使他剧烈摇晃。他的视线从灰色变成了黑色,过了一会儿,当他苏醒过来时,他听到了警笛声。老人终于死了,救护车来了,他想。他环顾四周。埃德在酒吧里喝了一杯酒,酒保也在他的岗位上,穴居人似乎没有抬头看一眼。呜呜呜呜,警笛响了。一股呕吐物拍打着他的脚。边水吐着血,把头枕在胳膊上,闭上了眼睛。
他们走出莱顿市政厅,走下台阶,沐浴在阳光下。维多利亚皇冠在停车计时器前等着,他坐了进去,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克莱尔才进来。她站在车旁,凝视着他,研究着他,就好像他是什么恶性的东西,是玻璃滑梯上的坏消息。最后她上了车。她咬紧牙关,肌肉绷紧,紧紧抓住钱包,仿佛那是她可以用来对付他的武器。
但是阳光是温暖的,边水闭上眼睛,把他瘀伤的脸转向阳光,吸收了阳光和他脑后热塑料的热量。
他能听到她摸索着拨钥匙。引擎启动了,他们就开动了。他们默默地骑了一会儿。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最后她问。
他睁开眼睛。没什么,他说。
你这个狗娘养的。你打算怎么还这笔钱?那可是我买摩托车赚的一大笔钱。
他什么也没说。
你打败了我所见过的一切。
边水掏出狱卒交还给他的那包皱皱的好彩香烟。他抽出一支,把它拉直,从打火机上点燃。他转过身来,注视着滑动的风景。他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乡村正在悄悄溜走,田野、石头和栅栏,奶牛就像无产阶级壁画上画的小奶牛。与西方世界相比,这是一种可怕的千篇一律。它滚到蓝色的地平线和更蓝的天空,那里被鲑鱼色的云隔开了。
你甚至都不会打电话给我。我不得不去那个可怕的酒吧找你听说你和一个老兵打架。你怎么了?我就该让你烂在那。
但她的手臂无力,石头也落得很宽,她的咒骂也落得很宽,这些咒骂最后不过是几句空话,而他听了太多遍,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似乎没有听见。窗户玻璃外,一个男人抓着转动着的犁柄,在一片漆黑的田野上走着,那么遥远,他仿佛在用某种虚幻的方式推着犁和骡子。埃奇沃特想知道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当他从地里回来时,他妻子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们隔着晚餐桌子谈了些什么。他会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后来,他会给他们讲故事,因为他们的眼皮变得沉重,睡眠像侵入的水一样在他们周围打转。一群画眉歪歪扭扭地旋转着,就像风吹在它前面的随机碎片。
我很清楚你是故意这么做的。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你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一走了之。你得把自己关起来毁了我的美好晚餐计划还浪费了那么多钱。
还有更多这样的事吗?他问道。
我真受够你了。最重要的是你是我见过最冷酷的人。我见过一些冷的。
“沿着这一带,我哪儿都可以出去。”
什么?
让我下车。
她锁住了刹车,车子滑到了路肩,开始在减震器上摇晃。边水镇逃了出来。一辆汽车在他们身后靠近。他转过身,伸出大拇指。在阳光下,那辆车似乎是从柏油路上翘起来的,迅速而闪闪发光,在短暂的阶段中变换着,仿佛它还没有变成真实的样子。它飞驰而过,没有减速,尾随着尘土和路边的纸张,这些灰尘和纸张在地面上悄然升起和落下。他继续说。过了一会儿,她把福特车启动,跟在他旁边,直到他下了路堤,爬过铁丝网,开始穿过田野。然后她停下车,对他大喊大叫,然后抱起一抱石头,开始向他扔去。但她的手臂无力,石头也落得很宽,她的咒骂也落得很宽,这些咒骂最后不过是几句空话,而他听了太多遍,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继续说。
的夜晚。冰冷的蒸汽像地面上的雾一样在地面上旋转。也许是午夜,也许是晚些时候,这似乎无关紧要。几小时前,最后一辆车让他在这条路上下车,他穿过了一个在这些封闭的时间里似乎无人居住的国家。连狗都没有叫。只是树林里不断传来刺耳的昆虫鸣叫声,在他走近时,它们沉默了下来,随着他的走过又飞了起来,是一只猫头鹰从遥远的木洞里飞出来,可能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这条路上什么都没有,他以为自己拐错了弯,但他突然想到,在这样的旅程中,没有错的弯。如果所有的目的地都是一个,那么你选择哪条路都无关紧要。在他所能看到的范围内,苍白的道路被月光淹没,在这些没有时钟的时间里,当事物的边缘模糊起来,心灵轻轻地拉着它的停泊处,在他看来,这条路以前从来没有走过,一旦他的脚步磨砺得越来越微弱,最终变得虚无,它就永远不会再使用了。
月亮升起来了,穿过银色和紫色的云。他的影子出现了,长长的,笨拙的,在看不见的电线上拖着,一个他在月光照耀下的路上跟着的陌生的孩子。
夜幕降临,天渐渐变冷了,他后悔地想起了克莱尔公寓里的外套和毯子,但那里没有衣服可穿。他上下打量着空旷的道路,但源头和终点都消失在同样寂静的银色薄雾中。他离开马路,小心翼翼地穿过树枝和黑莓丛,进入树林。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在一堆巨大的篝火前,成堆的浸过的树桩和枯枝,被连根拔起的雪松栅栏桩,还有铁丝的残根,像货运火车一样呼啸着,火花和燃烧的树叶在一个纯粹的热漏斗里倾泻而上。
他暖和了一会儿,然后坐在一根圆木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果,打开包装,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起来,强迫自己慢慢咀嚼,让它持久下去。烟盒里还剩两支烟,他点了一支,小心翼翼地把另一支藏在一边,明天早上再抽。他抽完烟,生起了火,躺下用圆木当枕头。
黑暗中一只夜鹰叫了三次,停了,夜鹰,夜鹰,夜鹰。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从树林的远处叫了一声,但第一个人保持沉默,好像他已经说完了所有要说的话。埃奇沃特闭上眼睛,那一天的画面在他的脑海里闪过,就像他正在看的一部脱节的电影。他慢慢地睡着了。
他的梦被搅乱了,他试图醒来,但做不到。在梦里,他在一家墨西哥旅馆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脸盆,一个五斗橱。喊声和粗哑的笑声从房间里传来,但这里没有人笑。这里有些地方出了差错。
床上的女孩浑身都在漏水。她全身铺满了猩红,仿佛她白色的身体躺在一朵巨大的美国美人玫瑰上,这朵玫瑰长得像癌症一样恶毒和畸形。那个老妇人和她那个穿罩衫的助手正准备逃跑。除了这艘船,什么船都选。那女人用他听不懂的西班牙语说了些什么,那男人也模仿她匆忙离去,把门半开着,在他自己逃走之前,他紧紧地靠在她的脸上,看着她眼皮的颤动,把他的手紧紧地夹在她两腿之间,好像他要把她拦住,不要,他说,不要,好像你对死亡有什么意见似的。
他想离开这个房间,走出这个梦他走到大厅,打开门,在他们各种各样的配对中惊讶的参与者中,一个女孩手跪在地上,被她的情人像狗一样骑在身上,转过身来,平静地在她的肩膀上研究他,乳房在她膨胀的手臂之间摇摆,她的头发像黑色的瀑布一样落下,当她的情人滑进她的身体时,她把目光移开,边水关上了门。隔壁房间里,一个水手正在把一瓶玫瑰发油倒进一个老妇人灰色茅草屋顶的阴道里;隔壁房间里,一个男人转过身去吹灭点燃窗帘的火柴,他朝艾奇沃特咧嘴一笑,眨眨眼睛,身后的薄纱窗帘像燃烧的牵牛一样爬满墙壁,玫瑰苹果色的墙纸卷曲着,冒着烟,散发着烧焦的肉般的恶臭。
他的父亲和他的妹妹在隔壁房间,老人睡在床上,妹妹陪着他。他憔悴的脸,他死前的气味。一个爬进窝里等死的老捕食者的眼睛。她手里拿着一块湿布,转过身去,边水镇看到老人一直在训斥她,她哭了起来。她丢下布,转过身去,靠在灰泥上。脱下衣服,她靠在石灰绿色的墙壁上哭泣。最后,她把脸转向她的哥哥,脸上带着悲伤和失落,他忍不住哭了起来。“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她说,他当着她的面关上了门。
他站在最后一扇门前,手里握着最后一个门把手。它摸起来是热的,似乎在他的手指下颤动,门的另一边有什么东西握着它。他意识到,在这扇门后面,躺着其他房间为他准备的东西。他鼓起勇气,深吸了一口烟雾,使劲拧门把手,把门推开,倒进了房间。
他醒来时浑身发抖,吓坏了,一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去过哪里。他用手擦了擦嘴。他用手掌捂着脸。上帝啊,他说。神。他仰起脸,紧紧地抱着自己御寒。火已经烧成羽毛状的白色灰烬,在微风中飘起,树间的蓝灰色光线有一种钢铁般的质感。
物体轻柔地涌现出来,树、树桩和长满苔藓的石头,对边角水来说,这些物体似乎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是存在的,这些东西第一次在他眼前诞生,他带着一种困惑的好奇研究这些东西。
他想重新生火,但他更想离开这片梦幻的林地,而不是温暖,他只停了一会儿,把灰耙掉,直到他找到一根发光的煤来点香烟。
当他从树林里走到路基上时,东方已经出现了微弱的玫瑰色的光芒,他通过第一次试探性的鸟鸣声继续朝那光芒走去。整个世界都在觉醒。所有的声音都是清晰的、等距的,在某个地方,一只公鸡预示着黎明的到来,在某条看不见的路上,一辆费力的卡车换了档。一轮红色的太阳爬上了树顶,用金色和银色的光吞没了地平线。
饥饿在他的胃里像拳头大小的一大块牙齿、爪子和破碎的骨头,但他的心正在上升,他的双脚感到轻快。这一天是全新的、未曾经历过的,这一天是从未存在过的,他把它看作一条小径,通向一个他无法理解的肉欲的、多方面的、复杂的世界,但此刻他在其中感到舒适,屋顶、遮蔽物和恶劣的天气都不重要。他认为他唯一需要的住所就是不受限制、没有围墙的世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