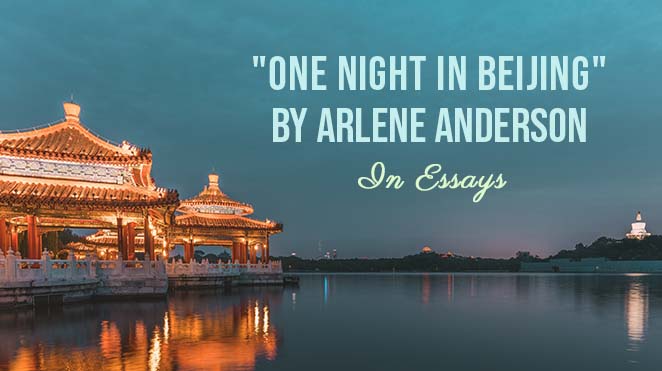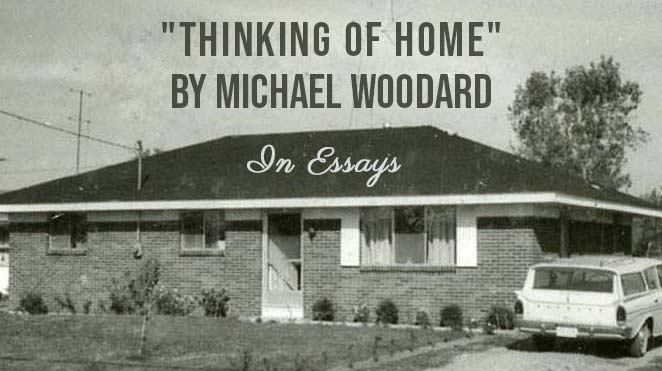大卫·哈德尔是七部故事集、三本小说、七本诗集和一本作家建议书的作者,是奥斯汀皮伊州立大学2012-13年度罗伊·阿库夫杰出教授。现年71岁的他并没有表现出放慢脚步的迹象:自2011年10月以来,哈德尔出版了一本小说,没有什么能让我这样做,以及诗集,黑蛇在家庭聚会上.他的作品已发表在纽约客,哈珀,最佳美国短篇小说等刊物。他曾两次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文学奖学金,短篇小说劳伦斯基金会奖和诗歌詹姆斯·赖特奖。
Huddle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也是一名优秀的设计师:38年来,他一直在佛蒙特大学教授创意写作,并继续在面包面包英语学校教授研究生。2月12日,在奥斯汀皮伊的小说朗诵之前,哈德尔回答了来自米兰通过电子邮件。
 米兰:你曾说短篇小说是你觉得最适合的形式,而诗歌更令人生畏;你花了很多年你说,“悄悄靠近它。”有了洛杉矶州立大学的一本诗集,美国首屈一指的诗歌出版社之一,你似乎不再感到害怕了。是什么改变了?
米兰:你曾说短篇小说是你觉得最适合的形式,而诗歌更令人生畏;你花了很多年你说,“悄悄靠近它。”有了洛杉矶州立大学的一本诗集,美国首屈一指的诗歌出版社之一,你似乎不再感到害怕了。是什么改变了?
大卫挤作一团我读得更多,写得更多,生活得更充实。我很幸运,在出版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所以我觉得诗人和读者群体给了我一定的认可。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了判断自己什么时候写的诗好,什么时候写的诗不好的能力。但我不能说我已经克服了恐吓。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渴望读那些感动我、教育我的诗,我认为我实际上在培养恐吓。当我遇到一首伟大的诗——即使是那些我多年来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读过很多次的诗(例如,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十一》,罗伯特·海登的《那些冬天的星期天》,罗伯特·哈斯的《拉古尼塔斯的冥想》,或者艾伦·沃格特的《歌与故事》)——我感到害怕。对我这个年纪的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幸福。成百上千的死去的诗人和许多活着的诗人,他们的成就明显高于我,而且永远高于我。阅读他们的作品让我变得更坚强。
米兰最近你写过一篇文章开头是这样的:“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模糊的不安。轻微的焦虑。偏执。痛打脆弱的自己。沉思的日子。”在干旱期间,你如何保持你会再次写作的信念?
我认为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是一种纪律,甚至是我试图送给读者世界的一种礼物。她把它说得像抽烟,或者试图引起注意,或者逃避社交场合。
挤作一团字体大约十几年前,我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与一位非常聪明而有权势的编辑交谈。他断言,写作是许多人的一种需求。我认为她的评论是一种科学观察,但由于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受到了一些赞扬的小说——而且我认为这是一项真正的成就——我把她说我这样做是出于需要的建议当成了一种贬低。我认为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是一种纪律,甚至是我试图送给读者世界的一种礼物。她把它说得像抽烟,或者试图引起注意,或者逃避社交场合。
我终于接受了她说的话。也许我没有需要在我二十五六岁开始认真写作的时候。但现在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知道我确实需要写作。就像我需要锻炼一样,我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我需要笑。所以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辜负了我的艺术,辜负了我自己。我的“信念”,我将回到写作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在过去,我总是回到它。但最根本的事实是我还会继续写作,因为我需要写作。需求的存在是科学的,但创造的需求本身是人类的精髓。鉴于我对自己的信念,听到我相信只要菲利普·罗斯的身体还能这样做,他就会再写一部小说,也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也许他很快就会这么做。
米兰约翰·贝里曼说,这位作家“非常幸运,他遇到了最糟糕的考验,但实际上并没有要了他的命。在这一点上,他是在做生意。”你对自己的苦难有同样的看法吗?
 挤作一团好吧,我很欣赏贝里曼的这一论断——他是那些“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有时让我害怕,但同时我又喜欢它——但他的生活与我的截然不同。我有过艰难的时期,甚至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认为这是一场折磨。我想他是对的,我确实觉得我在生活中被谦卑了几次,最终这种谦卑对我有好处。即便如此,我还是抗拒贝里曼措辞的戏剧性。我拒绝把它作为对作家的一般观察,而不是作为对他经历的描述——毕竟,他确实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自杀了。但如果我说同样的话,我知道我太夸张了。
挤作一团好吧,我很欣赏贝里曼的这一论断——他是那些“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有时让我害怕,但同时我又喜欢它——但他的生活与我的截然不同。我有过艰难的时期,甚至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认为这是一场折磨。我想他是对的,我确实觉得我在生活中被谦卑了几次,最终这种谦卑对我有好处。即便如此,我还是抗拒贝里曼措辞的戏剧性。我拒绝把它作为对作家的一般观察,而不是作为对他经历的描述——毕竟,他确实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自杀了。但如果我说同样的话,我知道我太夸张了。
我想不同之处在于,贝里曼说的是只有作家才会遇到的考验,而我所遇到的艰难时刻是普通的,几乎任何人都能遇到。也可能是因为我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所以我的写作方式更像工人阶级。我的最后一个想法是,贝里曼是那些开始创作杰作的诗人之一,这可能增强了他生活和写作的戏剧性内容。我不追求杰作;我只是试着在任何一天都尽可能地写好。
米兰如你打过电话了荣耀河你第一本诗集的"翻拍版"纸的男孩因为这些诗歌的最初出版版本或多或少地传达了“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后来的版本则是“一有机会就撒谎和夸大其词。”在你最近的作品中,你是否意识到对早期诗歌或散文元素的重做?
挤作一团:没有。实际上只有前半部分荣耀河是翻拍的纸的男孩那是因为我又写了半本书的诗,有点太努力了。幸运的是,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的《南方信使》系列的编辑戴夫·史密斯(Dave Smith)鼓励我删去那些不太成功的诗。后半段荣耀河是由大部分回避“谎言和夸张”的诗歌组成的。我认为荣耀河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接受“重拍”项目。我的倾向是继续前进,试着每次都写一些新的东西。
米兰:你的作品涵盖了大量的经历,有多种形式,有不同的声音。你认为自己是一种尝试其他形式的艺术家吗?还是说你更像是天生的多门语言者?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严肃的精神拷问。
挤作一团:我想我还是说“自然多语者”比较好。我没有太多的运气“计划”我要从一本书到下一本书写什么。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也写了很多,但最终有一半没有尝试出版。我在期刊上发表的很多文章最后都没有成书。我可以说,我对“创造性非虚构”这一新体裁为我打开的一些可能性感到兴奋不已——我希望能写更多这样的作品。我也比以前更像小说家了。但即使我精通多种语言,我实际上也是一种相当基本的艺术家——我创作叙事。
米兰:你把你的一些较长的诗描述为可与短篇小说相媲美的叙事或者个人论文。你如何决定用散文还是诗歌来讲述一个故事?
挤作一团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如果我的初稿一开始是一段一段的句子,之后几段都是这样,那么我写的东西很可能就会变成散文。如果初稿以行和节开始,并且在一定数量的行中保持这种状态,那么这篇文章将是一首诗。有一两次,我开始尝试用行和节来写作,但后来发现我真的需要用句子和段落来写作。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我在句子和段落的写作上走得很远,然后转向了行和节。如果我要改变,我更有可能从诗歌转向散文,而不是相反。我正在创作的作品通常在我开始作曲之前就已经知道它的性质了。
 米兰:自从40年前你开始写诗以来,世界或你自己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你写诗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米兰:自从40年前你开始写诗以来,世界或你自己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你写诗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挤作一团对于这个很难的问题,我将试着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我越来越相信,我必须把自己尽可能深入、尽可能直接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严肃的精神审问。我并没有对艺术的可能性失去信心,艺术可以产生对读者/观众/听众有价值的意义。也许变化不大,但在我看来的确如此。二十五岁时,我以为这全是聪明和技巧的问题;我已经71岁了,我很确定这完全是内心的问题。
米兰:您是否曾感到必须在教学和写作之间做出选择,还是两者总是相辅相成?
挤作一团字体在这方面,从1996年开始,我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当时我有幸在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弗莱彻免费图书馆(Fletcher Free Library),在银湾作家之声中心(Silver Bay Writer 's Voice Center)的赞助下,教授一个社区研讨会。该讲习班的所有成员都是具有显著的献身精神和成就的人。我们每周(通过投票)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作业,我和其他小组成员一起写作业。它的效果非常好——写作业并在我的兄弟姐妹的陪伴下大声朗读对我来说是如此令人兴奋——我在佛蒙特大学的本科教学和在面包面包英语学校的研究生教学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概念。在散文研讨会上让这种方法发挥作用在逻辑上是复杂的,但我已经学会了如何管理它。在我做出改变之前,我的写作和教学总是冲突的。我觉得为了对另一个负责,我必须对其中一个不忠。这种变化是我把写作融入到教学中——写作、教学和我的情感健康都得到了改善。
2月12日晚7:30,大卫·哈德尔将朗诵他2011年的小说《没有什么能让我这样做,在奥斯汀皮伊州立大学摩根大学中心303室从事。该活动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标记: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