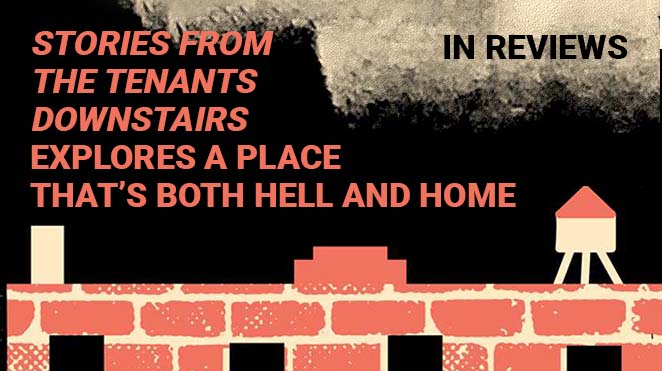在阵亡将士纪念日,我总会想起我的朋友,阿拉巴马州劳德代尔县的乔治·曼格鲁姆。下面是他的故事。它需要被告知。
1966年,我从一所普通的阿拉巴马高中毕业,开始找暑期工作。当时,民权运动正在撕裂南方,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吞噬了它所经过的一切。但那年秋天我获得了就读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奖学金,所以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在这个夏天赚点钱的机会。
 我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和一个全是黑人的工作团队一起从一个建筑工地搬运岩石和垃圾。像我这样的白人男孩在一个全是黑人的团队工作,在种族隔离的年代有点不太正常,但我很高兴能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的一些白人同学在他们父亲的公司做暑期兼职时,肯定会为此窃笑一番。
我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和一个全是黑人的工作团队一起从一个建筑工地搬运岩石和垃圾。像我这样的白人男孩在一个全是黑人的团队工作,在种族隔离的年代有点不太正常,但我很高兴能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的一些白人同学在他们父亲的公司做暑期兼职时,肯定会为此窃笑一番。
看到我,一个白人男孩,出现在工地,拿起一把铲子,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有点惊讶。他们对我并不冷淡,但他们似乎不确定,也许在想是不是老板派我来盯着他们的。但我默默地遵从了他们的想法,开始工作。
过了一两天,在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走近我,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乔治·曼格鲁姆(George Mangrum),住在县里的一个农场里。“这就是为什么其他人叫我‘国家’,”他说。他带着轻松而慷慨的微笑,把我介绍给其他船员,在他的介绍下,船员们开始热身。那些人试图念出我的姓,他们笑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开始叫我“白面包”。每个人都知道“白面包”是黑人对白人的嘲笑,但我不在乎。我们只是一起开怀大笑,然后我就加入了。
后来,我发现其他人都很和蔼可亲,乐于交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比我和乔治大,在我这个年纪,在黑人中,我对他们的年龄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很老,但很明显,他们一生都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乔治和我发现我们完全一样大。十八岁。乔治刚加入海军陆战队,整个夏天都在工作,直到他的征召文件来了。我一直在等九月份搬到纳什维尔,在范德比尔特开始新生活。乔治没有高中文凭——在他居住的地方没有黑人孩子上高中——但他并不担心自己可能要面对低工资的劳动生活。我们都没把未来看得那么远。我们当时只是孩子。
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很多话要说。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开玩笑,编造关于自己的谎言来打发时间。特别是,我们会吹嘘我们所有的女孩和酒,尽我们所能的夸张。乔治吹牛时特别有想象力,我们笑了一整天。
 那年夏天,珀西·斯莱奇在河对岸的肌肉浅滩成名工作室大获成功,乔治说他有个朋友和斯莱奇私交甚好。我们会一起大喊“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所有人都会笑。乔治和其他的人对斯莱奇的成功感到惊讶——他毕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低声谈论着据说他能挣多少钱。“啊,我记得那个孩子一无所有的时候!一个人不无骄傲地说。
那年夏天,珀西·斯莱奇在河对岸的肌肉浅滩成名工作室大获成功,乔治说他有个朋友和斯莱奇私交甚好。我们会一起大喊“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所有人都会笑。乔治和其他的人对斯莱奇的成功感到惊讶——他毕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低声谈论着据说他能挣多少钱。“啊,我记得那个孩子一无所有的时候!一个人不无骄傲地说。
于是,乔治和我成为了真正的朋友,只剩下了我们的本质,只剩下了我们自己,在亚拉巴马州夏天那令人窒息的高温和无情的阳光下。乔治的风趣和个性,他有趣的故事,古怪的观点和语言,让我越来越喜欢他,我很高兴看到他也喜欢我。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下班后我会邀请他和我一起坐在加吉斯商店的西瓜罐上,喝一杯Nehi。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种族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坐在外面阳光下的地上共享一桶午餐,但不能离开工作。
然后夏天结束了。我带着奖学金和学生兵役延期去了范德比尔特大学,乔治从海军陆战队拿到了征召文件。我不记得跟乔治说过再见,但我记得他为即将踏上人生冒险之旅而感到多么自豪。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都很兴奋。
然后,那年秋天,当我整天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书,参加派对和橄榄球比赛时,乔治发现自己在越南的杀戮战场上,带着一把步枪。
我的大学第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春天的时候我离开了学校,在科罗拉多州的林务局找了一份有趣的暑期工作。那对我来说是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暑假结束后,我在开学前回家待了几天,决定去拜访一下老剧组的人,看看他们都过得怎么样。我们将永远是朋友。
小伙子们见到我很高兴,但他们似乎很矜持。最后,他们告诉我,乔治大约一个月前在广治省某处的一次迫击炮袭击中丧生,那是一个没人听说过的地方。我目瞪口呆——乔治似乎不可能死了。我以前只是抽象地反对战争,现在却突然变得紧迫和现实起来。
男人们当然为乔治感到难过,但他们隐藏了自己的悲伤,用非裔美国人在那个严格隔离的世界里所需要的沉默的接受与我交谈。他们彬彬有礼,热情好客,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越过肤色界限远离我。乔治死于白人发动的战争,这让他们明白,去年夏天的田园生活不过是一场甜蜜的幻想,被一枚爆炸的炮弹炸得粉碎。
我一直后悔没有去拜访乔治的家人,尽管我从未见过他们,只从乔治的有趣故事中知道他们。但我觉得很尴尬。我害怕他们会怎么想。我是一个白人男孩,他们知道我享有特权,受到保护,安全回家。他们会理解,我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白人学校体系中接受教育,那里的老师让我相信我可以上大学,如果我上了大学,法律草案中有一个保护我的漏洞。当然,这些东西乔治都没有,他年轻的生命被扔进了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可怕的地方,最后在那场可怕而无用的战争的血腥绞肉机里被嚼碎了。
说乔治·曼格鲁姆为我而死太容易了。“这就是生活,”人们说,“抽签的运气,谁的名字在子弹上,一个人的命运”……诸如此类。但我不接受。当然,乔治的生命不止于此。但当我想到乔治·曼格鲁姆的一生,想到美国的特权、不平等和愚蠢的军事冒险,我就对理解绝望了。
也许我们从乔治短暂的生命中得到的教训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生。
但我爱你,乔治。也许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我会永远把我们在阿拉巴马州阳光下的劳动看作是美好的生活。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6年5月30日。]

版权(c) 2016由Wayne Christeson。保留所有权利。米兰克里斯特森(Wayne Christeson)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是一名退休律师,在田纳西州雷珀福克(Leiper’s Fork)的一个农场生活了25年。他的作品已刊登在范德比尔特杂志,纳什维尔艺术,纳什维尔的场景,失去了海岸审查,以及其他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