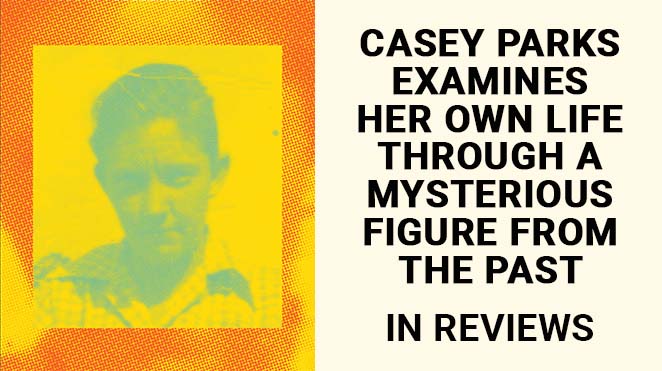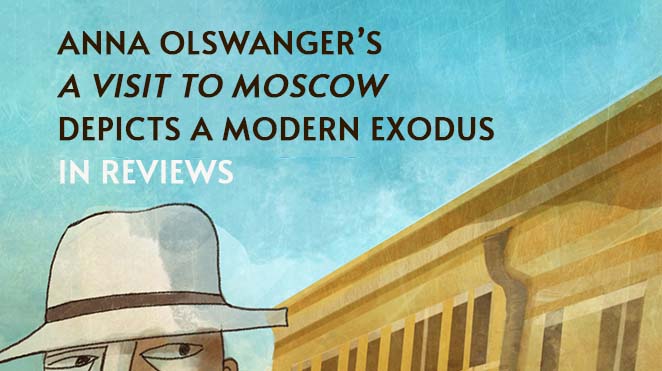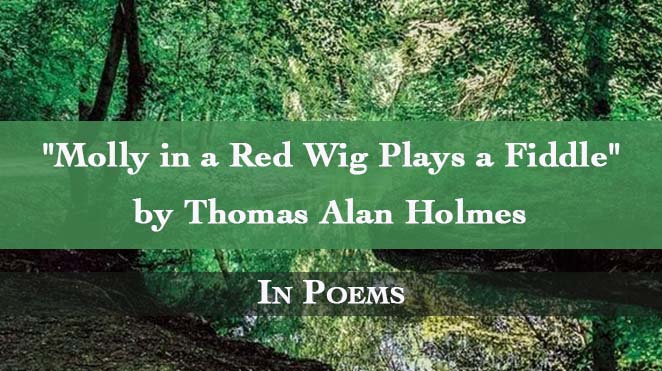沃利·兰姆的第五部小说是一个关于人心的动荡故事,也是人类生存能力的证明。在我们是水在美国,一个家庭几乎经受住了任何考验——抛弃、虐待、离婚、谋杀——因为爱依然存在。“我们就像水一样,不是吗?”羔羊写道。“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灵活多变。但也有很强的破坏力。”
兰姆之前的两部小说,她垮了而且我知道的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纽约时报》头号畅销书。我们是水讲述了安妮和奥里翁25年婚姻的破裂。安妮打算嫁给维维卡,代理她有争议的局外人艺术的经纪人。Orion的婚姻和他作为大学心理学家的职业生涯都崩溃了。
安妮和奥利翁的三个孩子不情愿地回到康涅狄格州参加安妮和维维卡的婚礼。就连奥利翁也在现场,她住在家里的老房子里,离安妮童年的家和夺去她母亲生命的那条河不远。在这本杂乱无章的小说中,兰姆用不同的声音讲述了安妮错综复杂的生活,直到他梳理出了最黑暗的一条,它第一次出现在她母亲死于康涅狄格州一场臭名昭著的洪水之后。
在出席纳什维尔公共图书馆Salon@615系列节目之前,沃利·兰姆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来自米兰.
 米兰:我们是水描绘了一幅家庭爱情的肖像,它在恐怖、虐待、离婚和再婚中幸存下来。对你来说,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是什么将家庭维系在一起?
米兰:我们是水描绘了一幅家庭爱情的肖像,它在恐怖、虐待、离婚和再婚中幸存下来。对你来说,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是什么将家庭维系在一起?
沃利羊肉:谁的家庭不必须经受住各种各样的挑战,从死亡、离婚,到爷爷去世后由谁继承爷爷的大钟?然而,尽管大大小小的麻烦,严重的和琐碎的,可能会浮到表面上,但爱的暗流最终会在除了最不正常的家庭之外的所有家庭中盛行。它是原始的吗?先天战胜后天?如果是这样,那么如何解释孩子和养父母之间深厚而持久的爱呢?我所知道的是,在家庭问题和创伤与家庭之爱的斗争中,爱几乎总是赢家。
米兰:两个她垮了而且我们是水揭示女人隐秘的内心。作为一名男性作家,你是如何创作女性角色的?你支持福楼拜那句著名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吗?
羊肉:这是我吗?不,夫人。但由于我是在姐姐和隔壁的堂姐姐妹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对女性的世界有一种最直观的看法。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既不投资于性别战争,也不投资于“女性的神秘感”。当你对女性开放时,她们也会对你开放,我想这就是让我可以自由地用我的女性角色的声音说话的原因。我不知道;如果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也许我就是一个星际旅行者。
米兰:你的两个主角之一吴安妮(Annie Oh)将她隐藏的痛苦和愤怒转化为具有挑衅性的局外人艺术。她和另一位外来艺术家约瑟夫斯·琼斯(Josephus Jones)都被自己的愿景所征服,并被强迫性的创作所驱使。你自己的写作是否遵循了这种创作模式?
羊肉:唉,这太少见了。对我来说,写第一稿基本上是一件苦差事。写下第一句话。修改了六次。写第二句话。解决它。回到第一句,再修改一下,等等。但有时我既不能完全描述也不能完全理解,我陷入了他们所说的“区域”,现实是我面前的书页或电脑屏幕上的东西,而不是我实际的环境或真实的生活。我想这是一种恍惚状态——感谢上帝,这是一种暂时的疯狂。
米兰:你一直住在康涅狄格州的诺维奇或附近,你是在那里长大的。当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羊肉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嗯?为什么我突然有了起床刮胡子的冲动?不过,说真的,我成长的城市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当地斯莱特博物馆(Slater Museum)的希腊和罗马文物展厅激发了我对古代神话的兴趣,这些神话是我小说的支柱。诺维奇有着丰富的美国原住民历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它是一个富裕的工业城镇,引进了数千名外国出生的移民在它的纺织厂工作。直到今天,这种多元文化的涌入以各种有趣的方式为诺维奇增添了风味。我最新小说的情节,我们是水,源于20世纪中期诺维奇发生的两起事件:1963年毁灭性的洪水和1959年一位名叫埃利斯·鲁利(Ellis Ruley)的非裔美国艺术家的死亡。鲁利是如验尸官所说的意外死亡,还是种族谋杀?
 米兰:在出版前的几周我们是水在美国,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50周年纪念日在电视上、报纸上和杂志上,在无数的私人和公共仪式上,在许多人的心中重演。考虑到种族主义的线索及其后果我们是水那么,这本书的发行日期是否计划与这个民权时代的提醒相一致呢?
米兰:在出版前的几周我们是水在美国,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50周年纪念日在电视上、报纸上和杂志上,在无数的私人和公共仪式上,在许多人的心中重演。考虑到种族主义的线索及其后果我们是水那么,这本书的发行日期是否计划与这个民权时代的提醒相一致呢?
羊肉:虽然我相信我的故事与1963年的大游行有关,并与它的半个世纪纪念日产生共鸣,但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发生。这需要一个策略,我是凭直觉写的,不是有策略的。有些小说家给故事提纲,并写一个预先设想好的结局。这使得他们可以像木偶师一样操纵角色。我的过程是不同的。我等着一个角色开口说话。然后,无论他或她决定带我去哪里,我都会跟随。所以,对我来说,主角就是操纵木偶的人,手里拿着笔,我就是木偶。也就是说,我确实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在真空中。我是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的头几个月开始写这本小说的,不断听到有人断言,我们现在是一个后种族社会。 I don’t buy that we can shake off the shameful aspects of our history that easily and brought that skepticism into the writing of my novel.
米兰当前位置您在诺维奇免费学校、约克惩教所和康涅狄格大学当了几十年老师。面对如此多样化的学生群体,你是否发现了学生写作的共性?还是关于写作?
羊肉当前位置1972年我开始教高中生时,分配给我的课是那些资深教师都不想上的。在我的高年级班里,很多孩子都被耽搁了很多次,有几个和我一样大:21岁。然而,当我邀请他们用他们觉得自然的声音写下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时,我们相处得很好。在她写了这首诗四十年后,我仍然记得她的一个学生芭芭拉·鲁利写的一首三行诗,是关于一个向她搭讪的男人的:一个高大高大的男人/戴着苹果帽,穿着三英寸高的高跟鞋/说的比收音机还多。(顺便说一句,我因为发表了芭芭拉的诗,诗里有“shit”这个词而和校长闹了一场。)
好的写作不在于拼写或撇号的位置。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好的写作依赖于诚实的声音。我的一个监狱学生,邦妮·佛雷弗,来自南佛罗里达的内城,她的演讲充满了当地文化的方言。例子:当两个女人在即兴的街头派对上聊天时,她们会“conversate”。然而,当邦妮进入我们的课程时,她的写作使用了一些小学老师可能坚持使用的生硬、假正式的英语。她在课堂上的谈话令人愉快,但她的书面作业却令人讨厌。邦妮,拿起那支笔,写在纸上,然后conversate我告诉她。一旦她这样做了,她的写作风格就被打破了,没有什么能阻止她。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0月28日。已更新以反映新的事件信息。]

莉达菲利普斯他是一位在孟菲斯长大的资深记者,曾在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学位。作为两本青少年小说的作者,她在返回纳什维尔之前曾为合众国际社工作。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