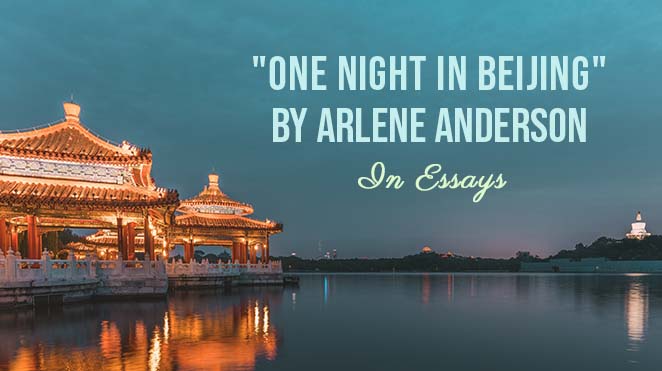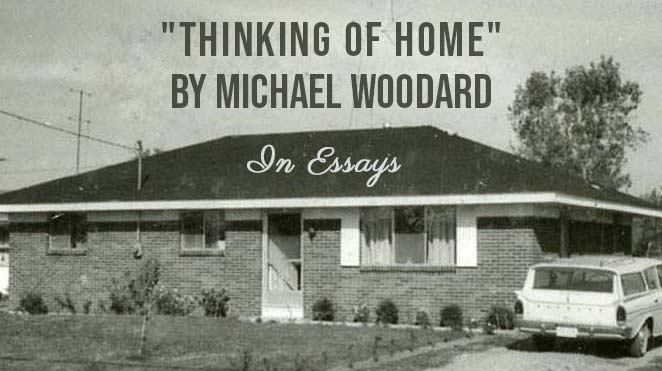在她1986年广受好评的书中,窃取语言:美国女性诗歌的出现阿莉西亚·奥斯克特(Alicia Ostriker)观察到,每一场文学运动“都植根于过去,它同时延续、否定和改变了过去。”这句话也可以用在奥斯克自己身上。作为评论家和诗人,奥斯克特从过去汲取灵感,质疑并重新诠释她的文学和文化祖先。奥斯特克拥有一种由男性主导的文学先神——威廉·布莱克和沃尔特·惠特曼在她的英雄中赫然赫然——所塑造的感性,并试图在她的诗歌中表达一种明显的女性视角。同样,在窃取语言在其他地方,她主张承认女性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传统,并指出作家“必须阐明性别经验,就像他们必须阐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种语言的精神一样”。
奥斯特克还对米德拉什作了大量的研究,米德拉什是犹太人重述或重新解释圣经的传统,目的是找到它与当代生活的相关性;或者,正如奥斯克特自己描述的那样midrash的意思是你把一个圣经故事编造出来。在父亲的赤裸:圣经的异象和修正(1994), Ostriker运用了诗歌、回忆录、幻想和分析的丰富组合,从二十世纪女权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和重塑圣经的故事。这是她个人的努力。在书中,出生于布鲁克林的犹太人ostriker描述了她对自己文化遗产的感受,她说犹太教中的厌女症“排斥我这个女人”,但她承认,“否认我的犹太教就像否认生命的礼物,否认悲伤的现实,否认学习和教学的乐趣。”
 奥斯克已经出版了十二卷诗集,其中两卷万物的裂缝(1996)和小空间(1998) -入围国家图书奖。奥斯特克的诗歌经常以感性和朴实的意象来探索社区和关系背景下的个人经历,比如“接近七十。”关于衰老和生命终结的思考,包括她最新的系列,七十之书.
奥斯克已经出版了十二卷诗集,其中两卷万物的裂缝(1996)和小空间(1998) -入围国家图书奖。奥斯特克的诗歌经常以感性和朴实的意象来探索社区和关系背景下的个人经历,比如“接近七十。”关于衰老和生命终结的思考,包括她最新的系列,七十之书.
在她1月26日在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朗读之前,奥斯克特回答了来自米兰通过电子邮件。
米兰你写道:“我不相信诗歌有治疗作用,但我认为它有诊断作用。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诗歌都能说明问题。”你也说过神秘是一种礼物。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中,你是否曾意识到神秘与清晰之间的紧张关系?
Ostriker:真是个好问题。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诊断”诗是“交流”,标题诗表面下的女人这本书出版于30年前。这首诗是根据我和孩子们一起划独木舟时的一个清醒的幻象写的,一个女神般的女性从水下升起,杀死了我的孩子们,然后回家杀死了我的丈夫,而我“与她交换了……游泳/离开,在凉爽的水中,遥不可及。”这种幻想让我害怕,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写了这首诗。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暴力,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在任何冲突的情况下总是感到无能为力,这首诗的暴力向我展示的是我有一个淹没的自我。一个被激怒的自我因为它被淹没了。我必须学会将女性的力量融入到我清醒的日常生活中,接受我可以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这是终身的任务。因此,这首诗本身显然是诊断性的——尽管同时它也在处理无意识自我的神秘。
另一方面,我刚刚读完托伊·德里科特那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殡仪馆老板的女儿在我看来,它既是诊断性的,也是治疗性的,因为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性的活动。所以我不想太教条。当然,诗歌对读者来说是一种治疗,即使对作者来说不是。
 米兰你被称为“女权主义革命者”。先不谈你自己是否接受这个称号,你认为诗歌或讲故事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成为世界上的革命力量?一个诗人带着革命的目的来创作,这合理吗?
米兰你被称为“女权主义革命者”。先不谈你自己是否接受这个称号,你认为诗歌或讲故事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成为世界上的革命力量?一个诗人带着革命的目的来创作,这合理吗?
Ostriker:女权主义者,是的,但我不喜欢“革命”这个词,这个词可以随便乱扔。当我想到“革命”时,我想到的是“极权主义”和“大屠杀”。法国,俄罗斯,中国——让我们把天堂带到地球上,哦,是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杀死数百万人。我认为我的作品是激进的,这是一个与根源有关的术语,但不是革命性的。
米兰:在窃取语言,你写道,“我们很少遇到赞美女性诗人的词语伟大的,强大的,有力的,精湛的,暴力,大,或真正的“女性的诗歌是否仍然以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美德来评判?”你认为女性诗人会继续感受到基于性别的期望的负担吗?
Ostriker在读完这个问题后,我发现自己坐在一桌子的人都是女性,她们都是我在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任教的低实习期MFA项目的学生,所以我做了一个非正式的调查。因为他们都比我小得多,我想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可能和我不同。没有。一致的观点是,女性被劝阻不要显得“过于雄心勃勃”。一位年轻女子说,她在10岁时决定要成为一名诗人,她改变了自己名字的拼写,让它看起来像个男人的名字。还有几个人说,他们曾考虑只用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在我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了女作家待遇的巨大变化,但我们还需要看到更多。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偏见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当然,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至少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是如此,所以它必须保持在地下。当然它也被女性内化了。女人不应该想要变得伟大、强大、精通等等。在语言中甚至没有女性版本的精湛的.它必须是什么?Mistressy?我们确实有一些很好的例外。我想到了爱丽丝·诺特利和安妮·沃尔德曼。
 米兰: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你说“大多数评论家不知道如何阅读”。你能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吗?
米兰: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你说“大多数评论家不知道如何阅读”。你能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吗?
Ostriker最好的评论家,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诗人。想想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塞缪尔·约翰逊、柯勒律治、雪莱、庞德、艾略特、兰德尔·贾雷尔、查尔斯·奥尔森、丹尼斯·莱弗托夫。有人记得名字或想法吗非诗人的批评?不过,这里也有例外。诺斯罗普·弗莱,一个非诗人,却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评论家。如果没有弗莱,我永远不可能理解威廉·布莱克在做什么。同意和不同意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都很有趣。但大多数学术评论家用术语来堵塞他们的散文,并隐藏他们可能有的任何个人情感。诗人往往会让他们对艺术的热情散发出来。也许,正如鲁米所说,只有那些感受过刀子的人才能理解伤口。
米兰:在为了上帝的爱,你写道,“我试图想象,如果各种类型的字面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读者都能理解,我们的知识、神学和教条的微小结构永远无法容纳上帝,那么全球宗教气候将会发生变化。”你认为这种改变真的有可能吗?有人认为宗教不可避免地会助长宗派主义和部落主义,或者说人类天生就会团结起来反对他者,对此你怎么看?
Ostriker我们的DNA不可避免地培养了部落主义。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本能地——我指的是生物学上的——和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在一起,不信任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说,意识到这一点并尽可能地抵制它是一个好主意。宗教为战争和压迫他人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理由,但民族主义也是如此。事实上,任何一种主义都可以成为打击别人的利器。但人类总会形成社会,总会形成宗教。宗教总是提供共同的社区,与比我们自身更大的事物的联系,苦难时的安慰,美丽的艺术作品,美妙的音乐,以及神圣感带来的欢乐。你猜怎么着——宗教还促进了对无助者的帮助,对有需要的人的慈善,以及社会正义的伟大运动。我们真的想生活在一个只有美元价值的世界吗?
米兰威廉·布莱克的作品对你来说非常重要,而你自己的很多作品都与幻想、预言和神圣有关。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特别轻视或敌视梦想家的时代?先知在当代世界还有一席之地吗?
Ostriker我可以用两个词来回答这个问题:艾伦·金斯伯格。金斯堡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一个预言家,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用他的热情、同情和慷慨改变了个人的生活,包括我的生活,他改变了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文学。是的,他甚至改变了世界。艾伦的岩石。
 米兰你在学术和艺术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来重塑你出生的传统。你认为一个艺术家有义务去面对她的本土文化中的不公正吗?
米兰你在学术和艺术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来重塑你出生的传统。你认为一个艺术家有义务去面对她的本土文化中的不公正吗?
Ostriker艺术家唯一的义务就是相信自己的执念,创作艺术。
米兰你能告诉我们一些你目前正在做的项目吗?
Ostriker: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生命之书:犹太诗选1979-2011》刚刚出来。这本书中的诗歌分散在八本书中,是关于家庭、大屠杀、以色列、精神追求以及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散居诗作。像许多犹太人一样,在会堂内外,我与神圣的传统搏斗,就像雅各与天使搏斗一样。我想改变世界吗?当然可以。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想改变我们对上帝的定义吗?是的。我相信,在史前时代,我们称之为上帝之父的存在吞下了上帝之母,就像《小红帽》故事中狼吞下祖母一样。就像在那个故事里,祖母没有死,我相信女神还活着在野兽的肚子里。我们可以在经文的地方看到她的足迹和痕迹,在那里她被不完美地抹去了。 I believe God is pregnant with his feminine self, and longs to be delivered. He’ll be less angry and judgmental when she returns to be his companion. I believe we can all be midwives, and bring her back—a notion I get from Lurianic Kabbala, where she is called the Shekhina. In Kabbala, whenever you perform a mitzvah, you are engaged in更美好你正在帮助实现上帝和他的Shekhina的团聚。这都是比喻,对吧?但我相信这是一个比喻。
我的另一个项目比较轻松。这是一组用一个老妇人、一朵郁金香和一只狗的声音写的诗。他们评论出生、死亡、性以及两者之间的一切。如果我们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他们可能重印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但我把他们看作人物,我永远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他们很有趣。
艾丽西亚·奥斯特克将于1月26日晚上7点在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校园的巴特里克大厅举行朗读会。
标记: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