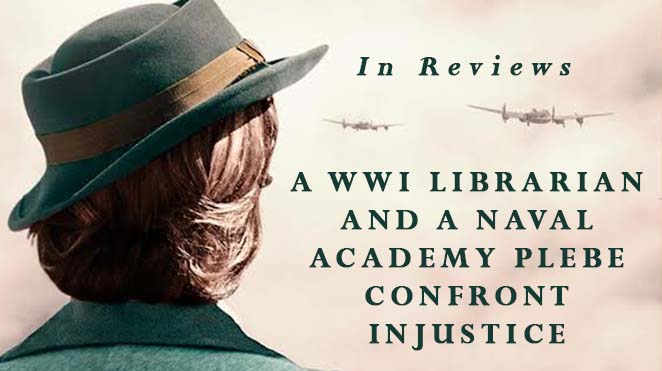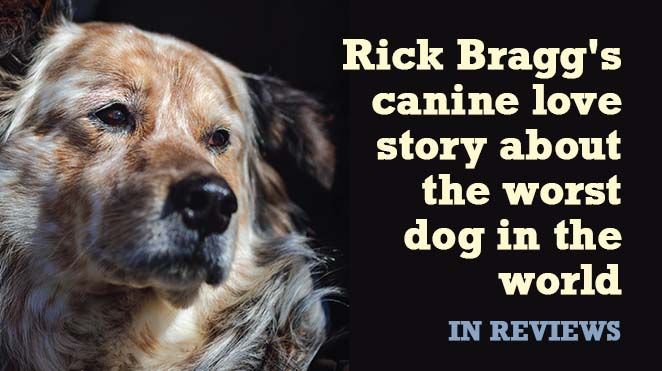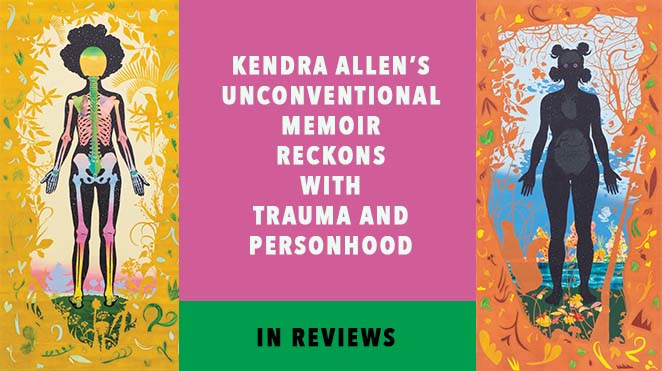"现在你看,我,一个身材高大,身材结实,但还没完全成形的年轻人,正当地开始了我五年的医学学习。——阿瑟·柯南·道尔记忆和冒险.

阿瑟·道尔把病人领进一个拥挤的煤气灯照耀的圆形剧场,穿过一群簇拥在约瑟夫·贝尔医生椅子周围的医学生,让他站在教授面前。这个人的态度是恭敬而不是卑躬屈膝。他没有摘下帽子。他用苏格兰口音解释说,他是来爱丁堡皇家医院治疗早期象皮病的。
像对待病人一样,贝尔医生一开始没有任何表情,他那矜持的神情在年轻的阿瑟看来就像是北美的一个红印第安人会有的样子。从孩提时代起,亚瑟就很喜欢美国边境的故事,这样的意象很容易跃入脑海。贝尔靠在椅背上,双手合十,仔细打量着病人,为了学生的利益,他说:“嗯,伙计,你在军队里服过役。”
“是,长官。”
“出院不久?”
“不,先生。”
“高地团?”尽管贝尔说话带着被称为“受过教育的爱丁堡”的清脆口音,但他的高音调与他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身体并不匹配,这让他看起来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
“是,长官。”
“non-com官?”
“是,长官。”
然后出现了一个似乎牵强的猜测:“驻扎在巴巴多斯?”
“是,长官。”
 病人离开后,贝尔解释了他的推论——这个人之所以不摘下帽子,是因为他曾在军队服役;他退役不久,否则就会恢复平民习惯;他的权威气质表明他是一名士官,而不是一名普通士兵。显然他是苏格兰人。“至于巴巴多斯,”他补充说,“他的抱怨是象皮病,那是西印度群岛的病,不是英国的病。”这位病人可能是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印度、阿富汗和西印度群岛——感染了这种疾病,但显然贝尔的推断是正确的。
病人离开后,贝尔解释了他的推论——这个人之所以不摘下帽子,是因为他曾在军队服役;他退役不久,否则就会恢复平民习惯;他的权威气质表明他是一名士官,而不是一名普通士兵。显然他是苏格兰人。“至于巴巴多斯,”他补充说,“他的抱怨是象皮病,那是西印度群岛的病,不是英国的病。”这位病人可能是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印度、阿富汗和西印度群岛——感染了这种疾病,但显然贝尔的推断是正确的。
贝尔之前除了收到阿瑟的病假条外,没有收到关于这个人的任何信息。尽管贝尔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和临床教师,也是维多利亚女王访问苏格兰时的私人医生,但他最著名的还是诊断技术。他倾向于在采访开始时,用他那双灰色眼睛的目光——半批评半讥讽地——从帽子到肘部再到靴子——来推断病人的病情、职业和生活的个人细节。他坚持认为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在病人说话之前应该了解很多情况。对于女性患者,他甚至声称,医生应该通过女性的姿势和握手的方式来预测她将要谈论的是她身体的哪个部位。
当他解释他的推理时,贝尔是在讲课,而不是在邀请讨论。19世纪70年代末,爱丁堡大学很少有教授和学生混在一起;有时与个别学生没有任何交流。许多人在学生面前坐着或站着讲课,讲课的要点由一群身穿深色外套、打着领带、一言不发的年轻人潦草地记在笔记上——有些人留着小胡子或大胡子,但也有许多像亚瑟一样把脸刮得干干净的年轻人。例如,亚瑟会付他的四基尼去上解剖学课,之后他会被要求勤奋地上课。然而,贝尔比大多数教授更有风度,对他的学生更感兴趣。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以及只要他们准备好上课的学生。
在教授了多年系统的外科手术之后,贝尔于1878年被任命为医院的高级外科医生。他是“课外导师”之一,这些教授并非直接受雇于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他们的课程被认为可以获得学分,以获得学位。贝尔自己的导师,传奇人物詹姆斯·赛姆,曾领导过一场认可校外教学的运动,最终在1855年获得批准,当时贝尔还是一名学生。这个项目在1876年亚瑟入学时已经很繁荣了,学生们可以在享誉国际的医院里和外科医生和其他人一起学习,也可以和总部设在外科医生广场公园学校、外科医生大厅、敏托学院和其他地方的医疗专业小组一起学习。他们可以在皇家公立医院、爱丁堡眼科医院、皇家妇产医院、儿童医院和城市的其他地方上课或接受其他指导。他们也可以在莱比锡或巴黎或其他公认的医科大学学习学分。
一群身穿黑色外套或粗花呢衣服、带着书和笔记本、看上去疲惫不堪的年轻人从医院大门涌向医院,用手杖敲打着石块,有时为了避开一辆在鹅卵石路上哐当哐当走下来的马车,他们会退到一边。在三翼的u型皇家医务室(Royal infirm)大楼里,有许多病房,其中两间病房的病人被认为对聚集在宽阔的中央楼梯上的学生具有教育意义,他们常常要躲避坐着轿子抬着病人的成对护士。“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衣服,”爱奥尼亚圆柱间的一条标语写道,“另一条标语说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慈善医务室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捐赠和订阅的高潮——在资金短缺的地方,玻璃制造商免费提供玻璃窗,工匠捐赠窗扇。医院于1741年建成,但事实证明,它无法救助大批受苦受难的穷人,于是,更多的建筑拔地而起。
阿瑟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一门课程和一位老师吸引住了。他急于帮助母亲度过经济困难时期——至少让她不必为他的大学费用买单——他试图把每年的课程都塞到半年里,这样他就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帮助医生,支付他的费用并积累经验。他急于求成,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充满好奇,草草写下了无数的笔记。在贝尔博士看来,阿瑟有时似乎想把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抄录下来。通常,在病人离开后,学生要求教授重复一些细节,以便他能把它们说对。
乔·贝尔——学生和朋友都亲切地称呼他——是亚瑟最喜欢的教授。他个子不高,肩膀棱角分明,鹰钩鼻,一张饱经风霜、面色红润的脸,在校园里和城里随处可见他的身影。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人们也能看到他那紧张而不平坦的步态——轻快的步伐战胜了跛行。
当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兼教师的职员给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学生一个很好的机会。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阿瑟机智、直率、勤奋;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摆脱早年的叛逆脾气。他的眼睛虹膜里有两种不同寻常的蓝色,和他的教授一样忙碌。
在开始在门诊病房工作之前,阿瑟就很欣赏贝尔那种戏剧性的诊断程序。每六个月,每个外科医生都会指派几个助手来帮助他处理交通问题。贝尔从许多年轻人中选择了亚瑟和其他几个值得信赖的梳妆师。阿瑟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除了临床外科成绩为s -外,其他各科成绩均为“满意”。但是贝尔认为他是他的学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个——一个对诊断的各个方面都很着迷的年轻人,一个对小细节的重大意义很关注的年轻人。外科门诊病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伤口或慢性疼痛,从呼吸系统疾病到妇科疾病。贝尔要求学生们为可能出现的任何不幸做好准备。新医务室于1879年建成,在接下来的一年里,15,000名病人通过了它的门诊。
阿瑟和其他办事效率高的办事员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接见病人,然后把他们迅速赶进赶出贝尔的检查室。他每天整理七八十个病人,记下他们的伤情和伤情的细节,然后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带进来问诊——在问诊期间,他常常认为贝尔一眼就能知道的比阿瑟询问了解的要多。当阿瑟开始当店员时,贝尔提醒他,门诊病人的面谈需要熟悉当地未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独特的苏格兰俚语。尽管他的父母是爱尔兰人,亚瑟出生在爱丁堡皮卡第广场附近的一栋三层公寓里,房子不大,但很漂亮,旁边是圣保罗和圣乔治圣公会教堂的哥特式复兴式胸墙。他向贝尔保证,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不可避免的是,阿瑟询问的第一批病人中有一个被证明是无法理解的:他抱怨说他的腋下有一块骨头。贝尔被逗乐了,他不得不向阿瑟解释,疼痛的部位是腋窝,而问题是脓肿。
“先生们,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推断,”贝尔自信地宣称,“你们可以对任何一个病例做出正确的诊断。”他为自己是一个聪明的观察家而感到自豪。“然而,”他会补充说,“永远不要忽视认可你的推论,用听诊器证实你的诊断——以及其他公认的日常诊断方法。”
贝尔会打量一个病人,漫不经心地说:“鞋匠,我明白了。”然后,他向学生们解释了,这是一个细节上的飞跃,而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注意到:病人裤子膝盖内侧有一块磨损的地方。这是一个修鞋匠把他的圆石放在那里的地方,在这块圆石上,皮革可以被锤打得更结实。
他向学生们指出了职业的其他线索,他坚持认为他们应该一眼就能看出。一旦他马上辨认出一个病人是割木板的还是割软木塞的:“只要你用眼睛观察一会儿,你就能看出他的食指一侧有轻微的硬化——正常的老茧,先生们,拇指外侧有增厚——这是他从事这一职业或那一职业的确切迹象。”
有一次贝尔的职员带来了一对母子。医生跟她寒暄了几句,漫不经心地问:“你从Burntisland回来是怎么过的?”法夫郡的一个小镇,在弗斯河畔。
“很好,”她回答说。
“你沿着因弗利斯街走了很久吗?”
“是的。”
“那辆车你怎么处理的?”
“我把他留给我在利斯的妹妹了。”
“那你还会在油毡厂工作吗?”
“是的,我是。”
贝尔向学生们解释了他相互支持的猜测:那个女人有法夫郡的口音,Burntisland是离法夫郡最近的城镇,这个女人的右手手指有一种burtisland油布厂工人特有的皮炎。“你会注意到她鞋底边缘的红色粘土,”他尖锐地补充说,“在离爱丁堡20英里的地方,只有植物园是这样的粘土。因弗利斯街毗邻花园,是她离利斯最近的路。”虽然她随身带着一件外套,但对于陪同她的男孩来说,这件外套显然太大了,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哥哥或姐姐。
“很容易,先生们,”贝尔在另一次场合说,“只要你们观察一下,把事实和事实联系起来。”
亚瑟的前任贝尔的助手之一,一个名叫a·l·柯罗尔的学生,和亚瑟一样崇拜贝尔,后来称他为“超人”。贝尔的家人同意这些学生的看法。当他和家人乘火车旅行时,他会观察其他乘客的细节,一旦陌生人离开,他会根据这些线索推断他们的私人生活,以此来逗孩子们开心。他会告诉他的孩子们那些与他一言未发的陌生人的职业和习惯,以及他们可能去的地方。后来他的女儿想起:“我们以为他是个魔术师。”

版权所有(c) 2016,作者:Michael Sims保留所有权利。迈克尔·西姆斯的六部广受好评的非小说类书籍包括亨利·梭罗历险记,夏洛的网的故事,亚当的肚脐他还编辑了《鉴赏家文集》,其中包括吸血鬼的客人,死去的见证,幽灵的教练,以及即将到来的弗兰肯斯坦的梦想.他是克罗斯维尔人,现在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