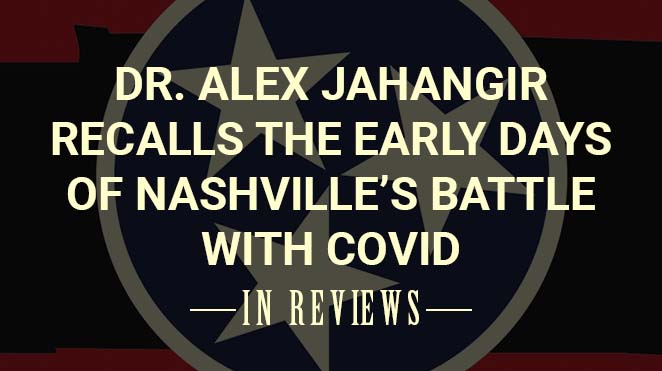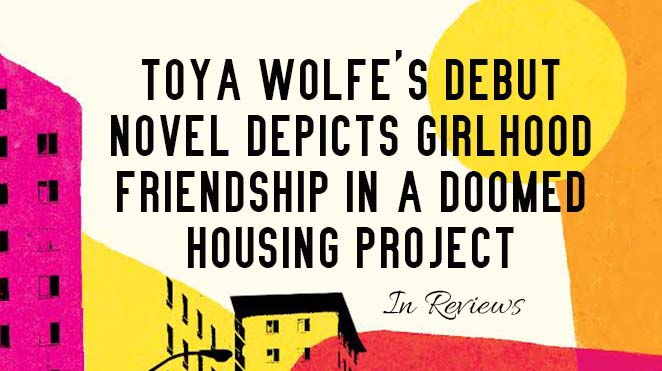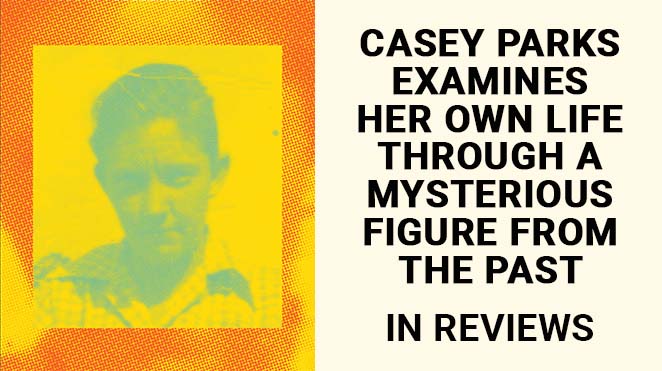我第一次读的是《诺克斯维尔:1915年之夏》的序言詹姆斯·阿吉的《家族死亡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我躺在东田纳西州一个与阿吉描述的很像的乡村社区的床上。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我的窗户第一次打开了。我能听到山下小溪里的窥视声,草丛里的蟋蟀声,狗吠声,孩子们在安全的黑暗中玩耍的声音。我也能听到我体内阿吉的声音。我出生在那里。他是我生命中的男人的声音: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叔叔。田纳西人,乡下人,他们熟悉夜晚,熟悉邻里,熟悉阿吉笔下的房子,“厨房里的母亲们洗衣服,晾干,收拾东西,像蜜蜂一生的旅程一样重复着她们的足迹。”
 读者经常认为詹姆斯·阿吉影响了我,而我几乎没有做什么来纠正他们的这种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保守着一个罪恶的秘密:我读过一些《家族死亡但不是全部。我有他通过他所影响的作家受到了阿吉的影响。比较起来很容易《家族死亡到科马克·麦卡锡的诺克斯维尔小说,Suttree这本书是我一次又一次寻求文学灵感的书。阿吉和麦卡锡是来自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他们用文字表达了一个紧密相连的社区和一个乡村小镇的粗犷底层的相同感受。在我看来,这两部小说也像是写给家庭的情书,写自渴望的地方。
读者经常认为詹姆斯·阿吉影响了我,而我几乎没有做什么来纠正他们的这种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保守着一个罪恶的秘密:我读过一些《家族死亡但不是全部。我有他通过他所影响的作家受到了阿吉的影响。比较起来很容易《家族死亡到科马克·麦卡锡的诺克斯维尔小说,Suttree这本书是我一次又一次寻求文学灵感的书。阿吉和麦卡锡是来自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他们用文字表达了一个紧密相连的社区和一个乡村小镇的粗犷底层的相同感受。在我看来,这两部小说也像是写给家庭的情书,写自渴望的地方。
但我并不后悔发现了《家族死亡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因为我可能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欣赏它。一定年龄的读者可能会以一种年轻人无法理解的方式认识到阿吉的奋斗——努力捕捉记忆,努力传达某些记忆带来的胸痛,“讲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悲伤。”当作者写到他的主人公杰伊·福利特(Jay Follett)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他是在说自己:“[M]记忆,几乎被捕获,无法夺回,难以忍受地折磨着他。”
《家族死亡这本书也许是为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可回顾的人写的,为我们当中想要得到某种东西又想要回到某种东西的思乡之人写的。当杰伊穿越河流,离开诺克斯维尔,前往他与生俱来的乡村时,他开始感到自己的出身把他拉回了过去:“这是现在真正的、古老的、深邃的乡村。祖国。”也许所有像阿吉一样,深深扎根于某个地方,被自己的出生地所影响的作家,都有一种类似的绝望渴望,想要回到真实的源头,在小说中讲述自己来自哪里的真实故事。
 但在他的小说中,阿吉并不是在努力再现一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他在把鬼魂写回生命。有一种真正的闹鬼《家族死亡在Jay Follett死在路上的晚上,他的妻子玛丽感觉到他的存在在他们的房子里。阿吉似乎在暗示,即使在死亡中,也不是一切都失去了。他似乎在问,我们还能从逝去的生命中保留些什么,我们还能保留些什么,哪怕只是写在一本书里。玛丽对她丈夫的鬼魂低语:“尽你所能和我们在一起。”我想,对阿吉来说,写作是一种坚持下去的方式。
但在他的小说中,阿吉并不是在努力再现一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他在把鬼魂写回生命。有一种真正的闹鬼《家族死亡在Jay Follett死在路上的晚上,他的妻子玛丽感觉到他的存在在他们的房子里。阿吉似乎在暗示,即使在死亡中,也不是一切都失去了。他似乎在问,我们还能从逝去的生命中保留些什么,我们还能保留些什么,哪怕只是写在一本书里。玛丽对她丈夫的鬼魂低语:“尽你所能和我们在一起。”我想,对阿吉来说,写作是一种坚持下去的方式。
阿吉也要求我们与死亡同坐,在死亡中安息,而杰伊的儿子鲁弗斯站在他的尸体旁的那一刻,几乎让读者——至少是这个读者——痛苦得难以忍受。我很想把那段令人痛苦的文字略过一遍,但我没有让自己这么做。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来到这一刻,如果我们还没有。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站在父辈的棺材前。这是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告诉我们的真相之一,是他在遗作《鬼屋》中捕捉到的失落、黑暗和乡愁的一部分。
这可能是最震撼的一幕《家族死亡鲁弗斯站在已故父亲的椅子旁,在“冰冷的烟草味和高高的椅背上隐隐的头发味”中徘徊。他的手指在烟灰缸里摸了摸,摸出来的“只有一点模糊的烟灰”。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装在口袋里或包在纸里。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舔了舔。他的舌头有黑暗的味道。”我们所失去的只是这些痕迹,但我们尽我们所能,留住了它。对詹姆斯·阿吉和我来说,写作可以是一种保存的行为。
最后,《家族死亡确实绕了一圈。故事开始于一个乡村社区,用优美的散文捕捉到修剪过的青草的味道,结尾是鲁弗斯和他的安德鲁叔叔“站在桑德斯堡的边缘,望着外面的荒野和土堆。”鲁弗斯的脑子里充斥着家庭和家人的苦乐参半:“他们爱他,但他恨他们……但他并不恨他们,真的。”可是,如果他这么恨她们,又怎么能爱她们呢?”我问过自己,关于我的人民和我在世界上的地位。你如何既爱一个地方又恨它?我们一直试图把它弄清楚,写下来,也许我们永远也弄不明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试图弄清楚我们与这些山和我们的人民的关系,我们与造就了我们的东田纳西的关系。所有的《家族死亡最后,阿吉用五个简单的词总结了这首歌。“该回家了。”

小说家艾米·格林是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者美洲血根草而且长人.她的第三部小说,火的本质,即将从克诺夫。格林和她的家人住在田纳西州斯莫基山脉的山脚下。

这篇文章是普利策奖百年篝火计划这是普利策奖委员会和美国国家人文理事会联合成立的一个项目,旨在庆祝2016年普利策奖成立100周年。我们感谢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公司、约翰·s·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普利策奖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对篝火计划的慷慨支持。
标记:小说,Pulitzer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