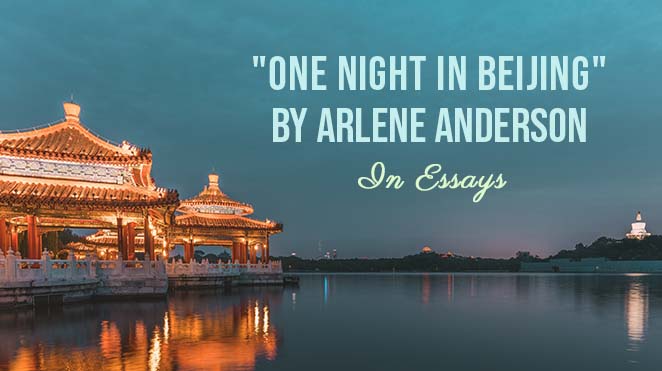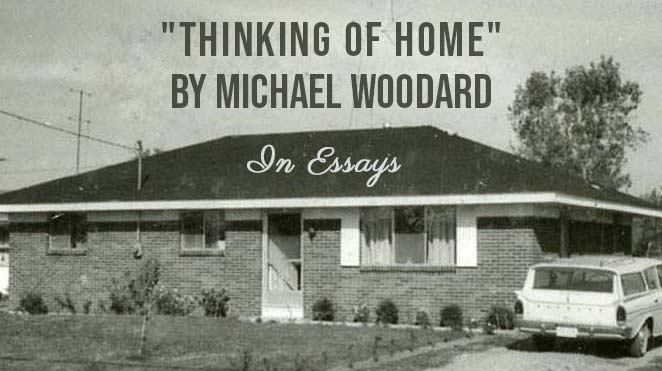Whuffo还没有跳伞的人,尤指观众。据说源自"为什么你会从一架完好的飞机上跳下来吗?”- - -跳伞指南
 当我爸爸喜欢上一个女人时,他总是邀请她来吃牛肉炖牛肉,而我必须在场。“最好让她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他说,包括他有一个16岁的女儿的事实。如果我的男朋友西奥,或者我的一个朋友,甚至是脖子上有纹身的科里,也可以过来。爸爸说如果她不能看穿科里身上的纹身,那她对他来说就太亲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朋友说我爸爸很酷。他们会觉得他很酷,即使纹身让他很不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他肃然起敬,事实上,他让他们的父母有点紧张也没什么坏处。
当我爸爸喜欢上一个女人时,他总是邀请她来吃牛肉炖牛肉,而我必须在场。“最好让她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他说,包括他有一个16岁的女儿的事实。如果我的男朋友西奥,或者我的一个朋友,甚至是脖子上有纹身的科里,也可以过来。爸爸说如果她不能看穿科里身上的纹身,那她对他来说就太亲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朋友说我爸爸很酷。他们会觉得他很酷,即使纹身让他很不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他肃然起敬,事实上,他让他们的父母有点紧张也没什么坏处。
晚饭后,爸爸播放“家庭视频”。故事的开头是一个四岁的小女孩——我——在空投区,穿着粉红色的连身衣,背着我爸爸改装成降落伞容器的背包。我穿着看起来像军人的小跳靴,就像以前跳伞运动员穿的那样。大多数时候,我爸爸的约会对象会说:“哦,她太可爱了!”我确实是。我的鼻子上有一堆雀斑,我的辫子是金色的,几乎是白色的,不是我现在头发的颜色——介于金色和浅棕色之间。不管怎样,四岁的我大摇大摆,好像这地方是我的。镜头摇晃着,因为我妈妈正在拍摄,她努力忍住不笑。
第一跳的学生静静地站在栅栏边,看着树冠打开,跳高运动员降落。他们知道他们很快就会登上大篷车,然后他们会爬到高处,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绑在我父亲或他手下的教官身上(教官会让他们保持稳定,打开舱盖,确保他们落在正确的地方,而不是挂在树上或挂在电线上咝咝作响)。然后,它们会一个接一个地降落,并大喊“呜呜!”and say that it was awesome and swear they’re coming back the next weekend. And then they’ll drive home and never make another jump.
这个视频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我觉得我还记得那天。我昂首阔步地在队伍中走来走去,看着最先跳的选手。两个女孩问我的名字和年龄,试图假装她们不害怕。我无视他们,走到那个看起来最苍白、最像要吐的人面前,我盯着他,直到他明显感到不舒服。然后我用我能发出的最诡异的声音问道,”你能闻到吗?”
这个人看起来很困惑。“我什么也没闻到。”
我歪着头嗅了嗅。我稍微提高了嗓门问:“你闻到了吗?”摄像机又摇晃了一下,你听到我妈妈发出一声鼻息。
终于有人问:“闻什么?”
然后我说:“死!”我像踩虫子一样跺脚,然后大喊"轰! "
我一直很好奇我爸的约会对象会作何反应。通常,她会紧张地傻笑。有时她会这样说:“天哪!”
我爸爸说:“我不知道是谁教她的。这对生意不好。”他听起来很严肃,但你能听出来他觉得这很有趣。
但我知道。我知道是谁教我的。我爸爸也是;我记得他生我妈妈的气,说她把顾客吓跑了。
在“轰!””the first part of the video ends because my mom cracked up so hard, she had to stop filming. The second part shows my dad doing formations in the air with his team the year they won the nationals, and then a world-record attempt he was in. That formation funneled right before the last person closed, but it was really pretty anyway.
最后是一则电视新闻报道,是关于我妈妈的团队在斯普林菲尔德大学的一场摇滚音乐会中做跳跃演示。我妈妈的伞盖是用线扭开的,所以她切得很低在她的备用伞打开前一个心跳就回到了自由落体状态。观众很喜欢。他们尖叫着,而记者则大喊着,说我妈妈离死亡只有几秒钟的距离,他们都目睹了一个奇迹。
新闻报道到此结束,但发给我爸的人给了我们未删节的版本,这让记者看起来很蠢。那个人问我妈,当她“坠向地面”时,她在想什么,她说:“我担心我的指甲断了。(她在逗他——我妈妈的指甲和我的一样短。)她摘下头盔,金色的短发被汗水粘在头上,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如此美丽,以至于人们很难直视她。记者一直试图让她说出她的生活在她眼前一闪而过,最后她以一种非常居高临下的方式说,“听着,伙计,这种事发生了。这是跳伞的一部分。你不会每次有人闯红灯或在高速公路上超车时都尿裤子吧?跳伞比开车安全多了,也比让跳伞运动员说话而不是让他们使用后台通行证安全多了。所以走吧。”然后她真的拍了拍他的头,让他站在那里,红着脸,看起来像他想哭。
然后爸爸总会拿出DVD,测试就开始了:每个约会对象都会根据她说的第一句话打分。她离开后,他告诉我她的成绩。我已经不再告诉他,根据一件事来评判一个人是荒谬的。我爸说如果一个女人不接受他跳楼,那就没必要再去见她了。鉴于他在降落区待了这么久,我想这是合理的。种。
大多数时候,他的约会对象说他跳楼是疯了。这为她赢得了一个d。他告诉她,他欣赏她的诚实,并没有试图说服她跳伞实际上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安全得多。如果他喜欢她的其他方面,他可能会再打电话给她。但他通常不会。
如果她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从一架完美的飞机上跳下来。”每个人对每个跳伞运动员都说,这是他们听过的最新颖、最机智的话,他会找借口提前结束约会。他甚至懒得给她一个标准的跳伞回答(“因为门是开着的”或“你显然从未见过跳伞飞机”)。"完美的飞机"这句话让她不及格,他再也不会给她打电话了。
如果他的约会对象说“那看起来真酷”,她就会以b通过。她不需要说她一直想跳——他有很多爱跳舞的朋友,更不用说他希望女儿永远爱跳舞了,只要她不介意他每个周末都在DZ度过,他就会和一个爱跳舞的女朋友相处得很好。但他不喜欢那些只说不做的跳伞运动员,所以如果她说她一直想跳伞,他会告诉她很好,下周六他会让她出去。如果她退出,她的成绩就会下降到c。如果她真的跳了,她的成绩就会上升到a,即使她讨厌这样做,并说她再也不会这样做了。“至少她努力了,”在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时,他说。
我爸爸的录像里没有一件事,那就是一段不稳定、曝光过度的录音,时长不到两分钟。我想他从来没见过——他不太会用电脑。有一天我在YouTube上搜索" jenna clancy最后一跳"就找到了。起初我没办法从头到尾看完,但试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看完了。然后我砰地一声关上电脑盖子,奇怪地想我把视频困在里面了,几天没有再上网。
每隔几个月我就会有一种发痒、焦虑的感觉,我知道我必须再次见到它。我一直等到我爸爸不在家。当我关着门待在房间里时,他不会来打扰我,但不知怎的,如果我和他一起看,我会觉得不舒服。
首先,我总是检查它有多少浏览量。我不去看那些评论——尤其是第一次,当人们说一些我希望我没有看到的事情,关于女孩跳伞,关于她一定会弄出一个多么深的坑。
不管怎样,录音一开始是我妈妈的四名比赛队员下飞机。起初它们只是小点。他们长大了一点,你可以看到他们正在练习全国赛的动作。他们身后的天空是如此明亮,以至于你几乎看不到他们结合成一颗恒星,然后是一个甜甜圈,然后是更多的编队,如此快速和精确,看起来不像真人,而像电脑动画。它很漂亮,但持续时间不长,因为跳伞者只有大约一分钟的自由落体时间。它们分开并相互拉扯。一、二、三棵粉红色的树冠在密苏里州蓝色的天空下绽放。
我妈妈最好的朋友,安吉,正在地上录音。她在演示队,但不擅长编队跳伞,所以另一个名叫米歇尔的队友代替了她的位置,这让安吉在比赛团队练习时没有太多事情要做。在视频中,她和一个你看不到的人交谈,通过他们的飞行方式来识别谁是谁。“那是帕齐……还有路易莎……和米歇尔。”她一开始听起来并不担心,她说:“现在詹娜在哪里?”她把镜头转了一圈,在一个黑点前停了下来,我知道那是我妈妈,但她的舱盖没有打开。相反,有一个凹凸不平的东西在她身后扑扇。
“这是珍娜。”安吉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安和紧张。“她——我看不出来——看起来像——是个包锁。”就是这样;顶篷卡在容器外面。我妈妈翻了个身。这应该能把顶篷拉出来,但没有。然后她又翻了一下,所以她的肚子朝下,很稳定,但树冠没有动。安吉开始叫道:“哦,天哪,珍娜,把它剪掉!快切,詹娜!” Another voice nearby yells the same thing, and even though my mom is obviously too far away to hear them, that’s exactly what she does, as though she’s following their instructions. She pulls the cutaway handle to release the risers from her rig, and for a second it looks like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but the main canopy doesn’t fly away like it should. It remains hung up, half in the bag and half out of it. My mom tries to clear it, but she doesn’t have much time, and then the automatic activation device on her reserve canopy deploys. But just at that moment the main canopy finally works itself free, and the reserve flies right up into it and catches its lines, tangling the two of them together.
两个树冠缠绕在一起,形成一条长长的漩涡——粉红色的主树冠和白色的备用树冠缠绕在一起,就像一些巨大的、致命的拐杖糖——我妈妈在下面旋转。她是如此的低,你可以看到她旋转,因为她猛拉绳索,从混乱的主缆中释放备用缆。安琪在尖叫,她一定是在跑,因为一切都变得颠簸和摇晃。然后她把相机掉了,你能看到的只有草,能听到的只有尖叫和哭泣。然后就结束了。

自由落体的夏天.文字版权所有©2018 by特蕾西·巴雷特.由查尔斯布里奇出版公司授权使用。巴雷特经常为米兰住在纳什维尔。自由落体的夏天将于2018年4月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