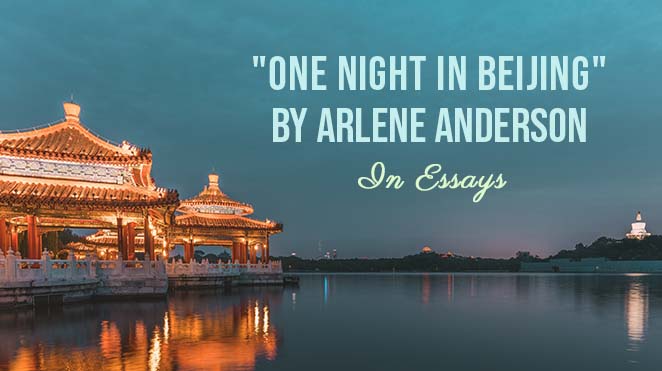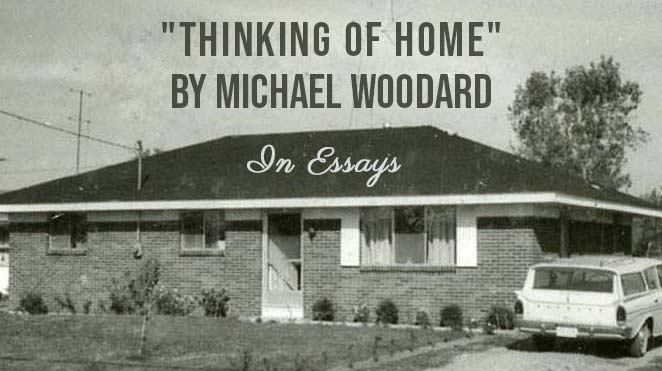1.保持警惕,活着到达
几年前,我意识到一件事:写作让我变成了一个鲁莽的司机。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发生了4次小事故,还有12次差点儿撞上。我追尾了一辆雷克萨斯SUV,在停车场倒进了一辆道奇Charger,在出口匝道上驶出了一辆福特金牛座。一天早上,我撞到了我妻子停在车道上的车。在旁道上,我没有注意到我开得有多快或多慢。我没有检查盲区,也不记得打转向灯就变道了。我渐渐习惯了按喇叭,咆哮着脸,竖起中指。我的保险费高得离谱。
 Glen Rose copy.jpg) 我不是像汤姆·威茨(Tom Waits)歌里的某个角色那样,在喝完酒之后才开车;恰恰相反,我的缺乏责任心的人这些生活方式早已让位于体面的中产阶级成年人:妻子和孩子,住在迅速士绅化的郊区,有一份教高中英语的稳定工作。我已经长大了,改掉了我的大部分恶习;在仅存的几个愿望中,除了写小说的愿望外,我都极力克制了。
我不是像汤姆·威茨(Tom Waits)歌里的某个角色那样,在喝完酒之后才开车;恰恰相反,我的缺乏责任心的人这些生活方式早已让位于体面的中产阶级成年人:妻子和孩子,住在迅速士绅化的郊区,有一份教高中英语的稳定工作。我已经长大了,改掉了我的大部分恶习;在仅存的几个愿望中,除了写小说的愿望外,我都极力克制了。
为了满足这种越来越可疑的痴迷,以及生活中更紧迫的要求,我开始了一种大多数非作家类型的人会认为荒谬的例行公事。周一到周五,我早上三点半起床,这样我就可以写作到六点半,然后我匆匆洗澡穿衣,帮孩子们准备好上学,然后匆匆穿过城市去上班。在上学的晚上,我尽量在九点半前上床睡觉,但即使我熬夜,我也会按响闹钟,下楼去工作。我相信我的作家生活就像鲨鱼一样:如果我停止游泳,它就会死。所以我继续工作,不管我能睡多少觉,经常带着危险的疲惫开车去上班,对世界来说,这并不比我和汤姆·威茨一起关闭酒吧更安全。
2.重新开始
我把二十几岁都浪费在假扮杰克·凯鲁亚克上了。最终,我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读了研究生,在那里我的习惯有所改善,尽管除了渴望成为一个像男人一样的作家(不管那意味着什么)之外,我仍然缺乏明确的目标感。我心目中的英雄是菲利普·罗斯和理查德·福特,科马克·麦卡锡和罗伯特·斯通,丹尼斯·约翰逊和鲍勃·沙科奇斯,他是我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导师,我对他就像一条鱼一样依恋。我花了很多时间做坏事,写了很多短篇故事——几乎都没有出版——然后开始写一部小说:一部西部黑色电影,讲的是一个酗酒的美国助理检察官和一个有前科的越战老兵,在新墨西哥州北部一个土地授予小镇的毒贩和腐败的当地警长之间被抓获。
读研究生一年后,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坚强美丽的女人,她唯一明显的缺点就是傻到下嫁。她的父母礼貌地接受了我,但带着可以理解的不情愿。(“一个作家?他写了什么?”)我们不在乎;我们相爱了,我要成为一名小说家。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妻子继续扮演着养家糊口的角色,并不断地啃我的代表作。
几年后,我的孩子快出生了,我成了ABD,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靠着微薄的工资当兼职教师。我们都想离开佛罗里达,我想在公婆家度假,而不觉得自己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几年前,我曾在一所私立学校短暂地教过书,所以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我们搬到了纳什维尔。
每个人都警告我说,在高中教书意味着我写作梦想的破灭,但我拒绝被挫败。花了几年的时间,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完成了那本小说,它好到足以引起一个特工的兴趣。尽管偶尔会有一些令人鼓舞的反馈(一位编辑把我比作丹尼斯·约翰逊!),但这本书还是毫无进展。
我的经纪人曾警告过我,她并不是每次都能卖出房子,但我对自己很有信心。这本小说里有所有我认为很酷的东西:酗酒和吸毒;堪比塔伦蒂诺电影的画面暴力;坚强,坚忍的男人在山上表现得很有男子气概。出了什么问题?
“再试一次,”我的经纪人告诉我。“你还年轻。”
是我吗?我马上就要37岁了。难道到现在为止,我不应该拿出点什么来回报我的努力吗?
一天下午,我的妻子和女儿和一个学前班的同学以及她的母亲一起玩完,回到了家。“你不会相信她对我说了什么,”我妻子说。
“什么?”
“艾德怎么样?’”she said, aping the woman’s sarcasm. “‘Still working on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没有什么比一记耳光更能让你清醒的了。再来一次,我想。如果我不能在四十岁前完成这一切,那就该离开了。
我加倍努力,重新开始。多亏了我荒唐的写作计划,以及一个赌徒把所有的积蓄都押在一个胜算不大的赌注上的愚蠢而狂热的紧迫感,我写了第二部小说,用了不到第一部的五分之一的时间就完成了初稿。编辑们很快对他产生了兴趣,但仍未达成协议。我的经纪人已经为我的事业投入了数百个小时,却只得到一分钱,因此他将是我一生的英雄。
她说:“我对这件事有良好的预感。”“有信心”。
半年后,在没有任何合同的情况下,我感觉到自己的四十岁生日正在逼近,我写作生涯的时钟越来越响,慢慢走向青春的尽头和希望的尽头。
一天,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我睡眼惺忪,心灰意冷地祈祷着。“亲爱的上帝,”我说,“如果你让我在四十岁之前出书,我保证优雅地老去。我要像个男人一样接受。”
几乎就在一瞬间,我的卡车驾驶室里充满了蓝光。我把车停了下来,坐在那里默默地生气,一个冷酷无情的警察给我开了一张超速罚单。
3.像个男人一样接受它
 任何认真写过小说的人都有同样的经历:牺牲时间和人际关系,严重的自我怀疑,失败、拒绝和羞辱时刻。我怀疑我是唯一一个为出书而祈祷的作家,但我可能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我的祈祷不仅让我收到一张超速罚单,还让我确信,如果真的有上帝能听到我们的祈祷,她就像我在高速公路上拦下的那些愤怒的司机一样,对我嗤之以鼻。
任何认真写过小说的人都有同样的经历:牺牲时间和人际关系,严重的自我怀疑,失败、拒绝和羞辱时刻。我怀疑我是唯一一个为出书而祈祷的作家,但我可能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我的祈祷不仅让我收到一张超速罚单,还让我确信,如果真的有上帝能听到我们的祈祷,她就像我在高速公路上拦下的那些愤怒的司机一样,对我嗤之以鼻。
我总是谦虚地讲这个故事——一个以我自己为代价的笑话,一个证明我对徒劳有多么谦卑的诙谐轶事,我变得多么善于接受自己的荒谬。但最近我注意到其中的潜台词,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作家这么多年来做错了什么。
“我要像个男人一样接受它。”我对自己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在生活和散文中犯下的许多罪过,都源于一种强烈的模仿浪漫主义、刚强反叛类型的作家的冲动,我很欣赏这些作家,但与他们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相似之处:比如凯鲁亚克(Kerouac)和卡萨迪(Cassady),肯·凯西(Ken Kesey)和巴里·汉娜(Barry Hannah)。我试着按照我想象中的他们的方式行事,按照他们的方式写作。我的第一本书——构思时带着坏态度、坏习惯和对自己不可避免的毫无根据的自信——实际上,本质上是对罗伯特·斯通的致敬狗的士兵但在美国,女性更少,暴力更多,也更不乐观。
三十五岁时,我再也无法保持这种幻想了。我不是亡命之徒。我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丈夫,一个老师,一个教练,一个年轻女孩的父亲。我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而不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我知道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所有儿童节目主题曲的歌词,也知道所有迪士尼公主和她们宠物的名字。我开始重视炖菜,《超人特工队》,精灵如同电影杰作一样《教父》而且《公民凯恩》.我戒烟了,喝酒也少了很多。我和我的女儿们、我的妻子以及其他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们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些硬汉和不法之徒在一起。当然,在我任教的男校里,我的工作时间都是和聪明、好奇的学生在一起。我调情的最大麻烦是在周五下午的欢乐时光和我的老师朋友们呆得太久了,回家又迟到了一场电影冻.
我仍然尊敬那些我试图效仿的作家们——尤其是鲍勃·沙科奇,作为一个作家和朋友,我欠他一笔无法偿还的债——但我不能再假装像他们一样了。于是,我回到了开始的地方:回忆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一个南方小镇长大的经历,在一个既典型又奇怪的家庭里。多年来,我一直回避那个地方,担心那里的土壤不够深,无法让我写出我认为自己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带着极大的恐惧,我抛弃了山里那些坚忍的反英雄,回到我真正感兴趣的、我担心的、困扰我的事情上:回忆与渴望、家庭与社区、爱与背叛、和解与救赎。
4.这和爱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在听尼尔·杨(Neil Young)的很多故事,他在我童年时期对我很重要,当时我的一些情节和人物都是基于他的记忆而创作的。又一个不稳定的早晨,在我上班的卡车上,我听着淘金热之后思考着我即将寄给经纪人的新小说该如何命名。这首歌变成了“只有爱才能让你心碎”。
就是这样,我想。只有爱才能让你心碎.
为什么不呢?这首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次要的情节装置出现在故事中,完美地体现了小说的情绪和基调。这是命中注定的。只有爱才能让你心碎是的,我想。
不久之后,我和一位作家朋友分享了这本书,他的意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那个头衔,”他说。“这有点女性化。你可不想疏远男性读者。”
我的第一反应是:哪些男性读者?当然,异性恋、白人男性的声音仍然垄断着奖项和评论页面,但我认识的大多数真正的读者都是女性,我遇到的大多数写作和出版专业人士也是如此。我的经纪人、图书编辑和出版商、这篇文章的编辑、我大多数作家朋友的经纪人和编辑、我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书店老板和员工——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超级聪明、有才华的女性。在文学界仍然有很多男人,读小说的男人——我是其中之一——但在我的经验中,他们不是那种因为这个词就把一本书扔在一边的人爱就在标题里。如今,如果你想让你的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那么明确地为大男子主义群体写作可能是一个糟糕的商业策略。
尽管如此,我朋友的话还是让我很痛苦。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已经想出了一种新的速记法:当人们问我的书名时,我很快就会提起尼尔·杨(Neil Young),重新树立我的男性忠诚。
我怎么了?
为什么我的朋友——我——我们——在心碎或爱情中看到了含蓄的女性化?难道这些事情对每个人都不重要吗?天知道,他们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5.走向更真实的小说
好吧,我回到了卡车里,身后是蓝色的灯,我有超速罚单,我上班迟到了。
“原来它!”我喊道。“谁能让我他妈的休息一下吗?!?!?”
有时候,生活给你的比你应得的更好。
就在那天早上——离我40岁生日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我的书被一位杰出的编辑和一群非常有才华和热情的人所接受,他们从那时起就以超出我最大期望的关爱和热情来爱护和培育这本书。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阿尔冈昆读本,我写道:“我认为,我们阅读和写作故事,是因为我们想弄清楚让我们困惑的事情——关于我们爱的人;关于我们的家庭和社区;关于我们被塑造和伤痕累累的行为和时刻。”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句话。但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没有遵守这些原则。我全神贯注地试图像那些我不认识也不像的人一样写作。我花了太多时间思考风格和技巧、形象和角色,什么是“严肃的”,什么是“不严肃的”,而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探索故事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让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在我的卡车里,我一直在昏昏欲睡地驾驶,这是一个危险的威胁,致命程度不亚于一个醉酒的人。但作为一名作家,我一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没有意识到我让自己失望的方式。
如果你不愿意在书中注入一点鲜血——或者大量鲜血,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文学技巧都是毫无价值的。长久以来,我一直害怕自己变得脆弱,害怕剥去那些诡计,去探究对我来说重要的东西的真相,害怕停止为酷而担忧,害怕从一个深深的渴望的空间写作,一个根植于记忆、欲望,最重要的是爱的空间。我再也不害怕了。
当我的经纪人打来一个重要电话时,我正在上一门课——美国文学荣誉课。我工作时不接电话,但这是一个我不得不接的电话。我走到我的桌子后面,轻声说话,试图隐藏我的兴奋,而我的学生假装没有偷听。当我放下电话时,他们期待地看着我。
“我刚把书卖了,”我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真的让我大吃一惊。男孩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鼓掌欢呼。我坐在我的桌子后面,脸红和慌乱,太高兴了,笑得停不下来。这是一个甜蜜的时刻,原因如下:当我意识到学生们眼中的骄傲和兴奋时,我想起了自己开始写作的原因——不是为了科马克·麦卡锡或丹尼斯·约翰逊或罗伯特·斯通,而是为了我内心仍然存在的那个男孩,一个充满希望、恐惧、爱和饥饿的男孩,他会熬夜阅读那些让他敢于梦想的书籍。

Ed Tarkington拥有弗曼大学的学士学位,弗吉尼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及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博士学位。他的处女作,只有爱才能让你心碎,将于明天由Algonquin Books出版。他住在纳什维尔。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