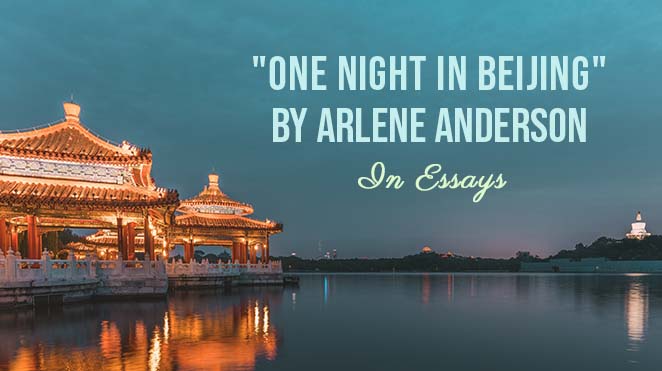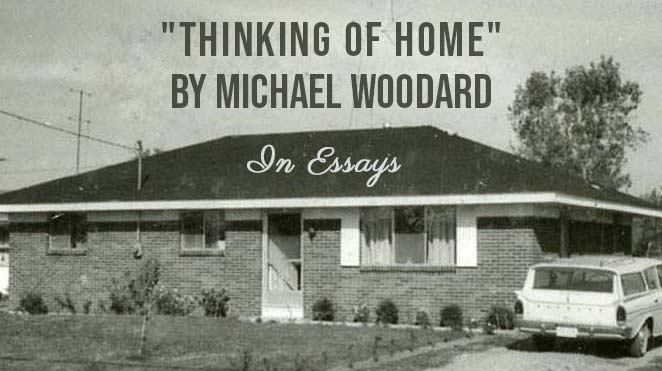影子
但是把这些记忆放在哪里呢?遮阳伞般的马利筋绒毛在汽车的背光下,低垂的太阳在家用砖上发出摄政般的光芒,但在汽车的金属上却闪烁着眩目的光芒。一只流浪的石龙子懒洋洋地躺在办公室的院子里,一只知更鸟在洒水器下着雨洗澡。可靠的是,那飘落的枫叶,它的影子如何奔跑去抓住它。
孕产妇
杀人鹿有一个聪明的计谋,破坏性的条纹打破了身体形状,并宣布:我不是鸟。你的眼睛看错了.对侵入者,他们佯装一种愤世嫉俗的伤害,一场带有求救的破碎翅膀的戏剧。但这些字谜是高尚的母性还是恐慌的短路?专家不同意。
秘密
这个场景没有音轨。坎伯兰高原寒冷的圣诞节早晨,天空一片白色,好莱坞最美的雪花慵懒地空降在洁白的地面上。我不记得打开了显微镜。但我记得我的尖叫,嗯,不,我看到自己口型无声电影的O,然后看向窗外,基顿的双视:显微镜下的雪花!
 所以这个昏昏的崭露头角的科学家,他跑出去拿了一把雪在显微镜下是水。两次,真是个白痴,滑梯从镜头下滑过放大了一个水坑。然后是真相大白,说服妈妈的喜剧场景,不需要对话标题,没穿外套就疯狂地冲出去,在显微镜冷却时瑟瑟发抖地蹲在地上。
所以这个昏昏的崭露头角的科学家,他跑出去拿了一把雪在显微镜下是水。两次,真是个白痴,滑梯从镜头下滑过放大了一个水坑。然后是真相大白,说服妈妈的喜剧场景,不需要对话标题,没穿外套就疯狂地冲出去,在显微镜冷却时瑟瑟发抖地蹲在地上。
下一个镜头,插入雪花?你知道,我觉得那个神秘的花边,那个凝固成护身符的气息——它的边缘太脆了。我想这是我读过的一本书。
但所有这些显微镜下的美丽秘密:蚂蚁是怪物。苔藓的树木。字母是页面景观中的峡谷。近距离看,照片就是你眼睛里的无数个漂浮物。我抬起头,一个卡通海盗,用我的单眼显微镜斜视着我们家和巴德家之间的小路上的腊肠犬斯基珀(Skipper)的晚餐大肚子——他在两个地方都吃过东西——然后我看了看妈妈的金属靴子盐瓶,在什么架子上,看着墙上的耶稣。我试着看这些点。哦,超人的眼光!然后回到隐藏的世界:盐粒就是小行星。
“我们吃石头,”我对弟弟说。
“你吃石头。”
月亮
我望远镜里的月亮影子。月亮像一个被抛出去的球一样逃离了光的圆圈,它在太空中的圆圈变得真实起来,就像在高地巷的弯道上斜靠向妈妈一样。还有一本关于池塘生活的袖珍野外指南,一张描绘光线折射的抒情图表——香蒲在腰部被切断,在水下它们的一条腿向一边倾斜:一个魔术师助手被锯成两半。对了,我的化学仪器是漂亮的玻璃试管,竖着放在支架里金属架、金属蓝白相间持有人。妈妈帮我调毒药。它把碗吃透了。
精灵
仍然在巴德和马特的院子里,仍然把那个塑料球扔给赫伯叔叔:他的眼睛只扫过一个香烟精灵,球在空中盘旋,在他的脚边砰砰地滚着,他低下头,又抬起头看着我。他只动了动眼睛。他的手臂肌肉不是在抽搐吗?我会接住,我发誓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会接住每一个扔出去的球。
但
但我没有。
跟踪
书页上的字母就像池塘里的足迹:妈妈一晚又一晚地翻译它们。我能感觉到她的声音从我的后背和侧面传过来。她的身体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当她深吸一口气时,我和她一起站起来。当故事生气时,她不呼吸。我也不知道。
快乐
很快,打字机按键在纸上刻字的喧闹快乐就开始了。
火焰
我们从斯巴达驱车上山,经过一家燃煤工厂,瞥见大门被橙色的火焰打开。
妈妈:“想想地狱会是什么样子。”
路径
夏天的夜晚,当光脚不再用盲文走路时,小路就忘记了房屋之间的路。现在妈妈独自坐在家里。夜晚小说只有一盏灯,但隔壁的树外一片漆黑,门廊上没有黄色的灯泡信号。黄灯曾经意味着马特生病了,或者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伊娃,或者来分享巴德从草湾带来的西红柿。
我没回家参加马特的葬礼。她讨厌医院和葬礼,讨厌疾病和死亡:多年来,她的亲人像恶棍一样围着她转。我仍然后悔没有去。六个月前我们在乔家见过他们,马特虚弱得像只老鸟,巴德笑着说他耳聋了,又喊着数着他乘坐救护车的次数。我握着马特的纸手。她给了我们一床结婚用的被子,我给她拍了照片,但忘了定焦。她的脸很模糊,但墙壁很牢固。
 我是9。沿着弯曲的小路,我赤裸的双脚在两盏灯之间的黑暗中找到了自己的路。鹅卵石是青蛙,然后不是。纱门上传来厨房纸牌游戏的笑声。巴德在碎石车棚里摆弄着冰淇淋机;他低低地坐在煤渣砖墙上,和我差不多高。
我是9。沿着弯曲的小路,我赤裸的双脚在两盏灯之间的黑暗中找到了自己的路。鹅卵石是青蛙,然后不是。纱门上传来厨房纸牌游戏的笑声。巴德在碎石车棚里摆弄着冰淇淋机;他低低地坐在煤渣砖墙上,和我差不多高。
他咧嘴一笑:“光脚走在黑暗里,你不怕吗?”
“不,我每天都在走这条路。”
巴德搬到养老院后,劳拉和我一到克罗斯维尔就去看她。他总是躺在床上,平躺着,蜷缩着,一个喉咙痛放学回家的小男孩。有时我们发现他睡着了,所以我们先去楼下看望他哥哥莱斯利的盲寡妇艾米。每次她抱我的时候都是在我九岁生日那天。然后巴德醒了,望着窗外冬天的白色天空,望着乔放在玻璃墙外的喂鸟器。就像拉斐尔(Raphael)的画作一样,窗户上有一只常驻的金翅雀。巴德笑得一如既往,耳朵却更加聋了,他大声地担心护士在他的巧克力牛奶里放了药。电视机静静地悬在我们头顶上。桌上放着两张贺卡;另一个躺下休息。 A ghost in the hall waves hello.
面具
蝉的皮肤像天使一样,可怕地躺在割下来的草和修剪过的树枝上,像病号服一样从背上裂开。我用我深情的手套举起这个幽灵。经历了一季战争的老兵,他的装备盔甲仍然变成了一个生命面具。
大天使
在高原上,一只黑眼睛的大天使,一只戴着雪肩章的条纹猫头鹰,从我们屋后树林里的一块墓地空地上冉冉升起。还有那片跳伞的枫叶。旋转。
返回
当我在黑暗中经过时,影视店的橱窗里挤满了名人的面孔,就像孩子们看雪一样。霓虹灯预示着一个永不黑暗的城市。但你看,那一轮新月,火山夕阳下的白色游艇。
从办公室政治到停车场里的欧椋鸟游戏。在大学学校玩耍的孩子们叫我的名字,我转过身,但他们没有看,那不是我的名字。鸟儿聚集在一起,它们的数量吸引着我的眼睛:像雪,灰尘,骚乱。一只欧椋鸟?就像那个故事里切斯特顿的邮差一样隐形,你知道那个故事。
然后在冬天的一天,他们以奇点交换,三三两两地回复黄昏,并合并成复数名词。手表:时间倒带。影片反过来,它们布满了树木,秋天的树叶又回来了。
鬼
今晨,经过冷雨和夜晚的寒风,我们的第一场雪,一层糖果粉,在门廊上融化成一层,而院子里的大石头变成了飞机上的落基山脉。其他乘客在睡觉。我凝视着云下炫目的山峰,在山坡上的Maxfield Parrish阴影之上。我羡慕那攀升的光,就像伽利略看月亮上的影子一样。他的蜡烛在风中熄灭,在我耳边吐出沙粒般的雪花。记忆、历史、白纸上的字母:那本打字机时代的旧笔记本,多年前浸在地下室的洪水里,上面雕刻着一排排的盲文,针孔般的感叹号,每一页上都是上一页的幽灵。
阅读迈克尔·西姆斯的采访翠鸟天,点击在这里.
版权所有(c) Michael Sims 2010。版权所有。
标记:非小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