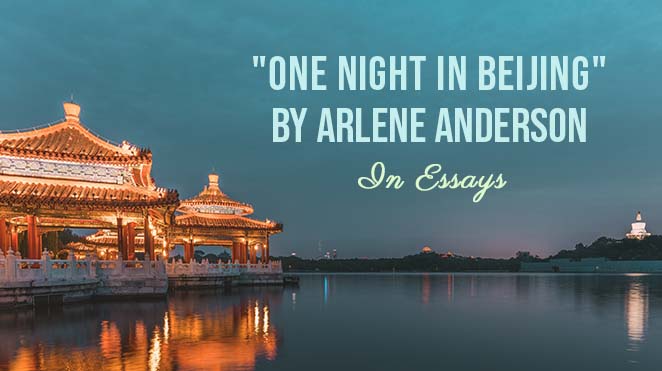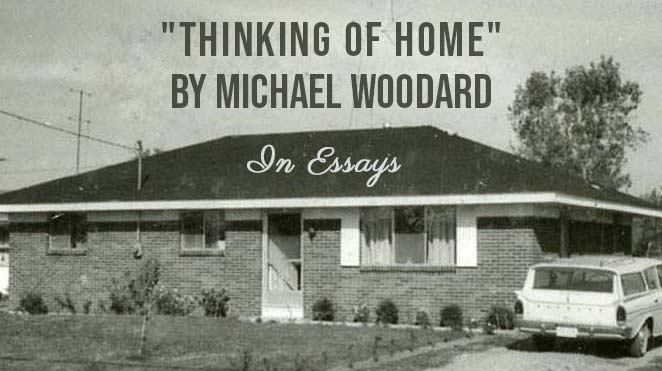对一些人来说,沙发是荣誉的徽章,是搭便车穿越美国旅行的纪念品,或者是通宵派对和在朋友家过夜的纪念品。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是战斗的伤疤,是另一场婚姻战争的象征。“是的,”你听到他们说,就好像他们为战友挡了一颗子弹。“睡在沙发上那晚上。”
有抱负的音乐家往往会对那些在沙发上度过的时光保持最感性的回忆,他们穿梭于全国各地,从一个酒吧或咖啡馆到另一个咖啡馆,指望陌生人的善意为他们提供一顿热饭和客厅里的一条毯子。我以前是一个创作型歌手,或者至少感觉像是另一个时代,但我没有在路上躺在沙发上的浪漫故事。不是因为订单没来,也不是因为唱片卖不出去,而是因为我做不到。我在沙发上睡了太长时间,一点也不浪漫。
我感到有点无家可归,就打电话给住在郊区的哥哥,问他我能不能和他住在一起。他有一张沙发。
父母离婚时我十九岁,随着婚姻的解除,他们在泽西城的房子也被卖掉了。我并不年轻,但我也没有大到可以独立生活的程度。我每天往返于大学和工作中来支付学费,我买不起自己的房子。我的父母各自在城里租了一套一居室的公寓,一开始我和母亲住在一起,还有她维多利亚式的塑料沙发。但是,是她提出离婚,是她想要脱离婚姻,很明显,她想一个人呆着。几个月后,我搬去和父亲住在一起,他的公寓在一栋相当新的大楼里,离他喜欢打牌的俱乐部只有一个街区,很方便。一个皮条客住在顶楼公寓里,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女人上下楼梯。这种安排只有一次出了问题——我的车被拖走了。登记在我父亲和皮条客的住址上,根据事实推断,警察指控我是皮条客。我试图说服他们我是一名大学生。 When they asked me if I had anything to with the “ladies down there,” I though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Margie in the financial aid office. How my Datsun 280 ZX wasn’t proof I wasn’t a pimp is beyond me.
我父亲不想离婚,当时的一切都让他很痛苦。他很痛苦,他会和我争吵,然后把我赶出去。很多个早晨,我都会躺在随公寓而来的硬纸板色沙发上,假装在睡觉,直到他去上班,只是为了避免和他打交道。然而,我错过了很多早期的课程,所以我回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没过多久,她也把我赶了出去。我搬回去和父亲一起住,现在他每天都把我赶出去。我有时会去女朋友家过夜,但她的母亲和继父都是酒鬼。有一次,我和她都睡在停在父亲大楼地下车库的达特桑汽车里。
受够了,又觉得有点无家可归,我打电话给住在郊区的哥哥,问他我能不能和他一起住。他有一张沙发。
吸烟可能对你有害,但当你需要远离某事时,它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起初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自己也经历了与已婚女人有关的痛苦。我已经是一个烟民了,我拿起雪茄和烟斗,只是为了证明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外面的院子里。吸烟可能对你有害,但当你需要远离某事时,它是一个很好的借口。终于,大约一年后,父亲打来电话,说他找到了一套两居室公寓,其中一间还带地下室,并让我和弟弟搬回泽西城和他一起住。那时,我快要大学毕业了,我的目标很明确:毕业,找一份全职工作,有自己的住处。
不到一年,我就做到了。我出去了。我在沙发上生活了将近四年,但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我有一张自己的床,还从救世军(Salvation Army)那里买了一张黄绿色的沙发和一张拉床,以防有朋友需要地方住。有一段时间,一位音乐家朋友做到了。
在这期间,我在新泽西和纽约各地播放我的歌曲。26岁时,我搬到了纳什维尔,想靠音乐谋生。但我不是个傻瓜。为了维持生计,我找了一份全职工作和一份兼职工作。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女人,并坠入爱河。三年后,我结婚了。我继续演奏和写歌,有时和我妻子一起,发行了几张获得了一些关注的独立唱片。2005年,我与纳什维尔最优秀的音乐家和几位客座歌手合作发行了一张唱片。这是我最接近突破的一次尝试。在国内和海外都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广播电台进行了健康的播放,而且还举办了真正有报酬的演出。 After months of discussion, my wife and I agreed that the time was ripe to give music a proper shot. And so I hit the road, playing gigs in Boston, New York, Philadelphia, D.C.
我还不够想要。我想念我的妻子。我想念我的床。
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在另一个音乐家的沙发上醒来,我意识到我做不到。在如此努力地工作之后,我不能再花时间睡在别人的沙发上了。这是一个如果你想睡觉就必须玩的游戏,有一天,在旅游巴士上或酒店房间里,我意识到我不想玩这个游戏。我还不够想要。我想念我的妻子。我想念我的床。
所以我停止了巡演,甚至不再参加当地的演出。我感到浑身瘫软。我的梦想破灭了,我需要重新思考我想做的一切,我想成为的一切。塑造一个新的自我需要一段时间。我及时地做到了,但我的婚姻受到了影响。
2011年,我和妻子分居了。我现在在西纳什维尔租了一间房子,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小办公室,还有我妻子不想要的破旧皮革家具。有些夜晚,孤独让我无法忍受,我发现自己睡在沙发上。但这一次却出奇地令人欣慰,让人想起了一个过渡时期,沙发只是通往更永久、更属于我自己的旅程中的一站。
版权所有©2013 by Joe Pagetta。版权所有。乔·佩塔是纳什维尔的一名作家和公关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