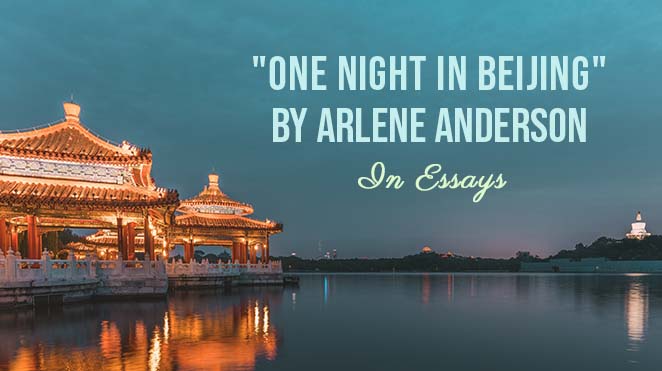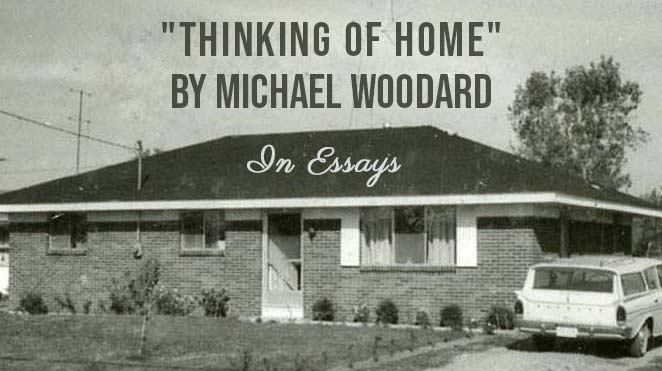就体裁而言,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威尔士的一个孩子的圣诞节》(A Child’s Christmas In Wales)可归入许多类别:故事、剧本、散文、诗歌、素描。对它的定义的困惑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首曲子是在记忆的抒情插曲中回旋,而不是在场景中朝着情节前进。当我第一次想到它时——在田纳西州一个孩子的圣诞节期间——我也不知道如何定义它。但就像伟大的故事有时会做的那样,“孩子”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定义了我。
 《孩子》让人想起了叙述者在威尔士海滨小镇斯旺西度过的少年时代的节日仪式。他所描述的事件闪烁着怪癖和季节性的欢乐。但《孩子》从托马斯的叙事声音中获得了真正的力量,这种声音充满了丰富性、神秘性和精神暗示。他抒情的散文让我明白了真正分享我们最难忘的记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我们试图传达这种体验的复杂性时,这种体验的丰富必要性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挫折。
《孩子》让人想起了叙述者在威尔士海滨小镇斯旺西度过的少年时代的节日仪式。他所描述的事件闪烁着怪癖和季节性的欢乐。但《孩子》从托马斯的叙事声音中获得了真正的力量,这种声音充满了丰富性、神秘性和精神暗示。他抒情的散文让我明白了真正分享我们最难忘的记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我们试图传达这种体验的复杂性时,这种体验的丰富必要性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挫折。
一开始,他就暗示我们陷入了记忆的陷阱:“所有的圣诞节都滚向两舌的大海,就像一个冰冷的月亮把我们的街道的天空捆起来;他们停在冰边的边缘,鱼冻住了,我把手伸进雪里,把我能找到的东西拿出来。”托马斯为我们提供了每一个瞬间,但讲述仍然是碎片化和虚幻的。
我第一次接触《孩子》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播出的一个小时的电视特别节目。这个来自英国的舶来品来到我的世界,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文学背景。沃尔玛没有提供任何装饰品或包装纸来描述叙述者遇到烟雾缭绕的前厅和戴着黄铜头盔的消防员,或者他看着两个被风吹着的威尔士人走向大海,或者他潜伏在下雪的街角,大口嚼着糖果香烟的那一刻。但我被故事的世界迷住了。
录像带是从电视上录下来的,由于过度使用,我们的录像带变得摇摇晃晃。在这个过程中,我那单调的纳什维尔后院变成了他“像拉普兰一样白”的雪景。我的塑料玩具变成了他的木制战斧和一营锡兵。我平时的叔叔阿姨们变成了他的——一群古怪的歌手和骗子,节日的馈赠和他们自己苦乐参半的过去。
丹霍尔姆·艾略特(Denholm Elliott)扮演叙述者,他沉思、脆弱的表情从欣喜若狂转为突然的悲伤,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他浑厚的嗓音将甜蜜的回忆与讽刺交织在一起,与观众相互配合,为家庭团聚或少年时代的冒险场景增添了故事本身所表达的色调深度和广度。
 我现在有两本很时尚的印刷版《孩子》——一本很小的故事书,大小可以挂在树枝上,还有一本浅蓝色的新航向出版社版,设计更时尚、更现代。这本小书里有弗里茨·艾肯伯格(Fritz Eichenberg)创作的迷人木版画,以圆润、夸张的细节描绘了故事中的关键图像。《新航向》的书以艾伦·拉斯金的木刻版画为特色。她的木刻为故事创造了一个更基本的景观,为读者打开了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假期回忆和托马斯的假期回忆。
我现在有两本很时尚的印刷版《孩子》——一本很小的故事书,大小可以挂在树枝上,还有一本浅蓝色的新航向出版社版,设计更时尚、更现代。这本小书里有弗里茨·艾肯伯格(Fritz Eichenberg)创作的迷人木版画,以圆润、夸张的细节描绘了故事中的关键图像。《新航向》的书以艾伦·拉斯金的木刻版画为特色。她的木刻为故事创造了一个更基本的景观,为读者打开了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假期回忆和托马斯的假期回忆。
但我可能是有意为之。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停止把我的度假环境与托马斯的故事结合起来,或者把他的故事元素吸收到我自己的故事中。每年,当假日季节的压力开始变得疯狂时,我都会想象自己正在《孩子》中描述的世界里漫游,以抵御这种压力:冬天的魔力,围绕着家庭成员和邻居出没的神秘事物,正常日程被暂停后的奇怪的时间弹性。
长大后,我追求着作家和读者的生活,我惊讶地发现,文学评论家们认为这个故事是感伤的,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童年的怀旧故事。即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当作一幅理想化的画像。相反,对我来说,似乎清楚的是叙述者试图将他的复杂记忆传达给另一个人的失败尝试。在叙事的不同阶段,他的年轻听众甚至声称自己理解了,但叙述者否认了这种可能性。积累了一个又一个细节,他一直试图说出他所记得的全部画面。
从一开始,我就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已经在我内心积聚力量的东西:讲述最重要的故事的动力,这些故事来自我们内心最深处。托马斯证明了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论断,即作家的生活是“通过艺术的迂回曲折,重新发现那两三个伟大而简单的形象的缓慢跋涉,他的心灵最初是在这些形象面前打开的。”托马斯的叙述者向我保证,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可能会继续走一些这样的弯路。
托马斯年轻时的斯旺西遭受了二战德国轰炸的严重打击。他所熟悉和经常光顾的许多景点后来都被摧毁了。战后的那些年里,托马斯创作了《孩子》的各种素描,他周围到处都是战争的损失,这可能放大了他为无法触及的过去寻找声音的动力。
对我来说,叙述者的童年被更黑暗的未知所笼罩,即使是最安全、最有爱的童年。托马斯可能描绘了一个充满雪景冒险和温暖富足的假日世界,但它幽灵般的边缘却回荡着古老的声音,燃烧着异教的火焰。所有在城镇里长大的孩子都能感觉到一种未驯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会把他们从家庭壁炉旁吸引走,让他们在狂野的冬夜中迷失。
这种危险也可能离我们更近——在我们父母疲惫的眼睛里,暗示着他们自己消失的童年的牵引力。或者在我们年迈的亲人难以想象的脆弱中。在他们的面前,有一种我们也许说不上来的恐惧,但它却徘徊在节日聚会的边缘。《孩子》中家庭团聚的光芒也体现了那些生活在这种温暖之外的人。在这所房子里,“有几个阿姨,厨房里不受欢迎,其他地方也不受欢迎,坐在椅子的边缘,泰然自若,脆弱不堪,害怕折断。”
 冬至季节的漫长黑暗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叙述者在圣诞之夜溜到外面和朋友们唱圣诞颂歌,“那时没有一丝月光照亮飞行的街道。”男孩们沿着一条很长的车道走近一个陌生人的房子,“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块石头以防万一。”在他们周围,“风吹过树林,发出刺耳的声音,就像洞穴里的老人发出的气喘声。”他们的恐惧是如此的奇怪,如此的自然,以至于可以召唤出原始的过去。
冬至季节的漫长黑暗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叙述者在圣诞之夜溜到外面和朋友们唱圣诞颂歌,“那时没有一丝月光照亮飞行的街道。”男孩们沿着一条很长的车道走近一个陌生人的房子,“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块石头以防万一。”在他们周围,“风吹过树林,发出刺耳的声音,就像洞穴里的老人发出的气喘声。”他们的恐惧是如此的奇怪,如此的自然,以至于可以召唤出原始的过去。
当唱颂歌的人唱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什么?“一个细小的、干巴巴的声音,像一个很久没有说话的人的声音,加入了我们的歌唱:一个细小的、干巴巴的、蛋壳般的声音从门的另一边传来:一个细小的、干巴巴的声音从钥匙孔里传出来。”
托马斯可能会把他的描述堆得很厚,但这种风格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人决心唤起他的全部经历——意思是,所有的经历。正如圣诞节本身是由其异教起源的残余所支撑,托马斯的威尔士山坡和海上城镇即使是最驯化的时刻也充满了神秘的、野性的一面。
他的声音混杂着神圣与狂野的冒险,死亡与重生——我们生命的伟大循环。他施了一个咒语。所有童年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当一个咒语被施下时,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则就会弯曲和改变。新的规则开始生效,在我们被它的咒语所控制的时间里,故事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的世界。
假日季节常常要求我们屈服于它的魔咒。在那些喜庆的几周里,我们按照它的规则生活。圣诞颂歌从每个公共演讲者中响起,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数量惊人的季节性商品和装饰突然出现。无论我们是欢迎这种感官超载,还是害怕它的到来,不可否认的是,假期改变我们的体验,坚持这个世界的意志。对我来说,经受住最严酷的商业化大惊小怪并不意味着全盘拒绝。相反,我试着去寻找那阴森的边缘,去倾听那些古老的声音,从我们嘈杂的、灯火通明的现代庆典的边缘向我们低语。
就在几天前,我坐在那里观看梅西百货(Macy 's)的感恩节大游行(Thanksgiving Day Parade),这是一个我情不自禁地喜欢的季节性活动,尽管我时不时会按下静音键。我想起了我的祖母——一个三个月前去世了,另一个还活着——都90多岁了。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他们的故事深深地吸收到我自己的神话中,然后开始质疑细节,让他们把故事再讲一遍。我发现自己忘记了我父亲的母亲——一个令人难忘的缪斯女神,我的心肯定是在她面前第一次打开的,加缪式的——已经不在这里了。
第二天,我母亲的母亲无法回忆起她的重要记忆。母亲和我沉浸在令人不安的沉默中,帮着讲一个我们都很珍惜的祖母少女时代的故事,这个故事我还想再听一遍:有一天,在她父母的农场上,她惊慌失措,跳过一条生气的响尾蛇,投入了惊恐万分的姐姐的怀抱。然后他们都看着他们的大姐拿着铁锹冲进来,砍下了蛇的头,救了他们。
我和母亲一字一顿地说出了每一个细节——一条蛇在阿拉巴马州的泥土中嘎嘎作响,两个小女孩尖叫,一个英勇的姐姐把武器举过头顶。我们变得过于急切,也许,紧紧抓住我们强烈的需要来唤起她的记忆。我们有可能在那一刻改变了历史。也许是蛇变大了,也许是女孩们变得更年轻、更无助了。我们看着她听着这个来自她自己生活的奇迹故事,为它的发生而震惊,为它从她的脑海中溜走而震惊。
现在我已经试着告诉你这个故事了,但我知道我还没有接近。我知道我还得再试一次。
在节日期间,旧年与新年、光明与黑暗、成年与童年之间的某些面纱会变得薄薄的。托马斯理解这种季节性的心理状态。随着《孩子》的最后一段结束,叙述者从那个不可知的夜晚跑回家,在家人的簇拥下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夜晚。他爬楼梯睡觉。他听着楼下那些爱他的人之间播放的音乐,这些人总有一天会离开:“我对着亲密而神圣的黑暗说了几句话,然后我就睡着了。”

Emily Choate版权所有(c) 2019。版权所有。艾米丽·乔特拥有莎拉·劳伦斯学院的艺术硕士学位,是Peauxdunque审查.她的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已在谢南多厄河谷,《佛罗里达评论》,山茱萸的季度,Yemassee,深夜图书馆,以及其他地方。她住在纳什维尔附近,正在那里写一本小说。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