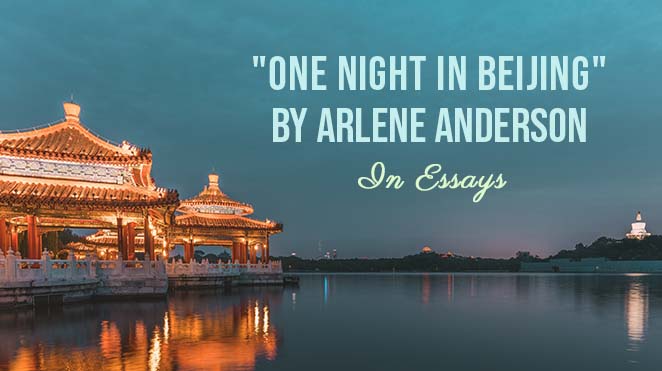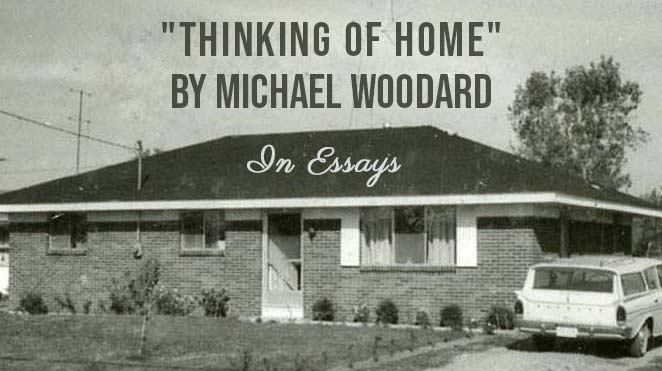如果我不得不不幸地选择最后一餐,我会选择一份火腿三明治和一杯加牛奶和糖的茶。这是我在文法学校的时候和奶奶一起吃的午餐。我去了泽西城高地区的圣尼古拉斯。学校离我们住的房子只有几个街区远——我妈妈、爸爸、哥哥和妹妹住在顶楼;我奶奶和爷爷住在一楼。我祖父在我八岁的时候去世了,就在我开始走路上下学的时候。

我的祖母,我叫她“保姆”,会在我回家吃午饭时为我准备好三明治和茶。我们会聊各自的心事,然后她会让我带着25美分的硬币回学校。在我家和学校之间的拐角处有一家杂货店,回来的路上,我会用这25美分买一袋Wise薯片。
保姆不是我的亲生祖母,但她是我唯一认识的祖母。我父亲的父母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我母亲14岁时,她的母亲死于胆囊手术并发症。我祖父留下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其中一个有智力障碍,还有两个小儿子。他知道他需要帮助。大约三年后,他遇到了玛丽并与她结婚,他和我母亲以及她的兄弟姐妹称她为Mae。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在曼哈顿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工作,后来成为我母亲的导师,把她介绍给纽约和艺术,并帮助她找到第一份工作——在摩根大通担任私人秘书。她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我的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
她的孙辈也是如此。她充分利用了我们离纽约很近的优势,把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装在她70年代末的蓝色Nova车上,带我们去泽西城中心的自由州立公园,然后坐渡轮去埃利斯岛和自由女神像。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想我们夏天需要做点什么,她很乐意做我们的监护人——她可能有很强的历史感,这些旅行是她向我们介绍历史的方式。和我们一样,她也是意大利后裔。她的祖先和我们的祖先一样,受到同样的自由女神像的欢迎,走过同样的埃利斯岛。我们也许不是血亲,但我们来自同一个血缘。
她也很有趣,尤其是在实地考察时。有一次她在回家的路上追尾了另一个司机。那家伙下了车,走到她驾驶座的窗户前,开始用西班牙语对她大喊大叫。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她平静地从钱包里拿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用英语告诉他,去给自己买瓶汽水。他不知所措,沉默了下来。然后他拿了钱,走回他的车里。

我19岁时,保姆死于脑瘤并发症。当她躺在客厅的病床上时,母亲在我和妹妹力所能及的帮助下照顾着她。我们的午餐仪式早已结束,但她的去世引发了我们家庭的变化,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从未从中恢复过来。我母亲的家庭破裂了,父母也离婚了。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分道扬镳了。回想起来,我母亲显然已经在与未确诊的情绪障碍和早发性痴呆作斗争。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火腿三明治配胡椒芝农场面包,再来一杯加牛奶和糖的茶是我最后一餐的最爱,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为什么。当然,这是安慰的食物,带我回到和保姆在一起的那些迷人的下午。但这也是“以前”的味道。之前的隔阂。前痴呆。之前的经历。
我妻子和我有一对一岁的双胞胎女儿,是在一位卵子捐献者的帮助下怀上的。去年年底,我岳母搬来和我们一起住。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安排。她在房子的一边有自己的房间和浴室,我们在早上和晚上,在工作之前和之后都有内置的帮助。我们都省钱了。还有一些不那么有形的好处,比如我岳母每次早上走进厨房或下班回家,看到那两个小脸对着她微笑时的喜悦。
最大的赢家是我的女儿们,她们可以和Honey(她更喜欢被这样称呼)在一起,就像我可以和Nanny在一起一样。星期五只属于他们,而且总是有很多来回的闲聊。像保姆一样,霍妮可能不是血亲,但从她爱女孩的方式,以及她们爱她的方式,你永远不会知道。
时代变了。每天在白面包上吃火腿,然后再吃一袋薯条,这已经不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午餐了,即使有点老派的霍妮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所天主教文法学校,我希望几年后我们能供孩子们上得起。也许有些事情并没有完全改变。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有“之前”和“之后”。我希望我的女儿们永远不用面对“之后”,但至少我知道她们正在经历我能想象到的最甜蜜的“之前”。
 版权所有©2017乔Pagetta.版权所有。佩佩塔出生于新泽西州泽西城,是纳什维尔的散文家和艺术作家,她的作品曾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纳什维尔的场景,美国,PBS.org,媒体的转变,纳什维尔艺术,我的现代Met如果你算上他给小说家卡伦·麦肯(Colum McCann)关于自己时尚品味的信的摘录——《时尚先生》.
版权所有©2017乔Pagetta.版权所有。佩佩塔出生于新泽西州泽西城,是纳什维尔的散文家和艺术作家,她的作品曾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纳什维尔的场景,美国,PBS.org,媒体的转变,纳什维尔艺术,我的现代Met如果你算上他给小说家卡伦·麦肯(Colum McCann)关于自己时尚品味的信的摘录——《时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