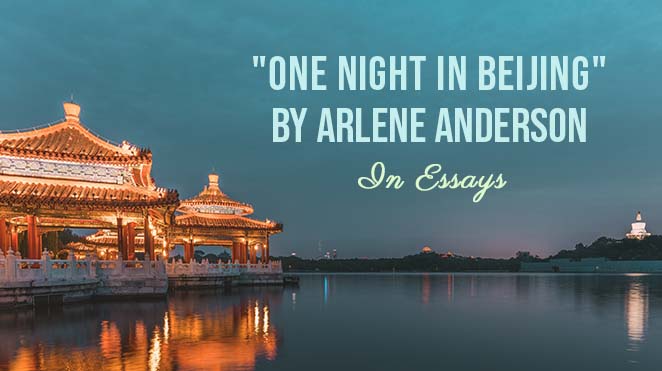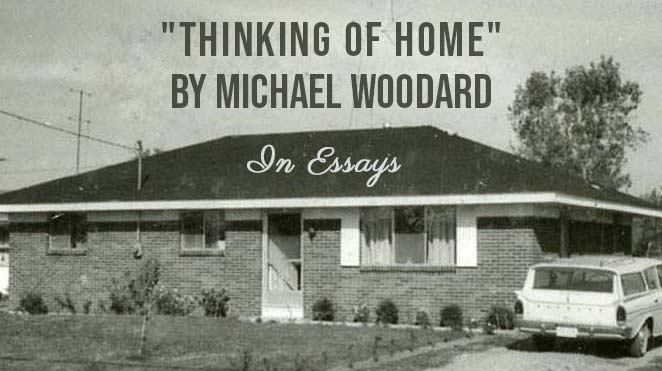艾米·亨佩尔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在埋葬阿尔·乔尔森的墓地里》是这样开头的:“告诉我一些我不介意忘记的事情。”
 这是20世纪最被选集的故事之一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开头。当我们得知这个请求来自叙述者身患绝症的最好的朋友时,这句话就被一种新的失去和爱的感觉、回忆和哀悼所困扰。亨佩尔对她作品中句子层次的声音的关注,意味着阅读她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几乎是音乐般的体验,节奏和脉搏似乎与故事本身的发展一起影响着读者。
这是20世纪最被选集的故事之一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开头。当我们得知这个请求来自叙述者身患绝症的最好的朋友时,这句话就被一种新的失去和爱的感觉、回忆和哀悼所困扰。亨佩尔对她作品中句子层次的声音的关注,意味着阅读她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几乎是音乐般的体验,节奏和脉搏似乎与故事本身的发展一起影响着读者。
她对句子的注意使她的故事受到关注。她曾获Rea短篇小说奖、Pen/Malamud短篇小说奖、美国奖学金和古根海姆奖等荣誉。她获奖收集的故事(2006)收录了她出版的四部作品,活着的理由(1985),在动物王国的门口(1990),内倾(1997)和婚姻之犬(2005)。人们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短篇小说是长篇小说的热身作品,但亨佩尔证明,与长篇叙事相比,短篇小说与诗歌的基因密码更相似。她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浓缩,有时甚至进入散文诗的范畴。有几个故事不过几句话:在她的第四部文集《回忆录》中,她写道:“我一生中只有一次——哦,我一生中什么时候想要过一次?”
部分因为这些极短的故事,亨佩尔经常被贴上极简主义者的标签,与雷蒙德·卡弗、玛丽·罗宾逊和戈登·利什等作家齐名,后者是她在70年代师从的著名编辑。然而,“极简主义”暗示着一种渺小,亨佩尔更喜欢“精确主义”,雷蒙德·卡弗(Raymond Carver)用过这个词。她的故事捕捉了小时刻的精确纹理,并揭示了它们的巨大,因为这些小时刻积累了更大的感觉。她的小说《收获》(The Harvest)也被广泛选集,她在书中写道,“当我讲真话时,我漏掉了很多东西。我写故事的时候也一样。”
如果亨佩尔为了接近真相而略去一些东西,那么写亨佩尔的故事就会遗漏一些在纸上经历这些故事的真相。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容易概括,大多数角色甚至没有名字。在《要约》中,结尾的故事故事集,亨佩尔的匿名叙述者指出了她的情人对她讲述的故事的偏好:“对他来说,名字不是细节。重要的是我们行动的最精细的特殊性,以及我的叙述的陈述性。他不希望我使用的语言不符合事实。”
 亨佩尔自己作为作家的目标也是如此。但是,《要约》中情人提出的要求,就像《在埋葬艾尔·乔尔森的墓地里》中朋友表达的要求一样,也说明了为什么亨佩尔的许多故事都让人感觉像是在读一封来自远方亲爱的朋友的信。它们让我想要回信,想要回应。
亨佩尔自己作为作家的目标也是如此。但是,《要约》中情人提出的要求,就像《在埋葬艾尔·乔尔森的墓地里》中朋友表达的要求一样,也说明了为什么亨佩尔的许多故事都让人感觉像是在读一封来自远方亲爱的朋友的信。它们让我想要回信,想要回应。
虽然这些故事有时有一种人类声音呼唤另一种声音的氛围,但它们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人类声音。亨佩尔写了一些感人的纪实作品,讲述她的志愿者工作,她把小狗养大,给盲人当导盲员;她还与作家吉姆·谢泼德共同编辑了释放:作家的狗的诗歌,在这本书中,作者从他们的狗的角度写诗。在1997年《炸弹》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她说:“据我所知,动物不会在讽刺或讽刺背后隐藏真实的感觉。”动物的存在使她的人类叙述者更加诚实和脆弱,不那么冷漠。
这并不是说这些故事从来都不有趣,部分幽默来自于它们拒绝遵循短篇故事的传统结构。对于亨佩尔来说,典型的情节线——上升的动作、高潮、顿悟的瞬间——似乎太过做作,不够逼真。在《附件》中,叙述者凝视着她家对面的墓地,看着那些开着推土机清理成排坟墓的人。“那些开着推土机和其他东西的人不把他们正在清理的东西称为一排,”叙述者指出。“他们称之为情节线。”
在《翻滚回家》中,亨佩尔拥抱的不是线性的情节线,而是平凡的时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事实,在一次死里逃生之后,我们都接受了平凡。但那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奇迹。或我们我——我要活着去看看。”如果亨佩尔的故事能帮助读者拥抱平凡,那么它们也能让读者感觉更有活力,把我们的日常认知变成更接近敬畏和奇迹的东西。

李·科内尔的处女作皮层下最近获得了故事奖聚焦奖。她的小说曾在肯扬审查,格尔尼卡,线列车,美国短篇小说.她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获得了艺术硕士学位,现居住在纳什维尔。
标记:小说